著名核科学与技术专家,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陈达先生,1937年出生于江苏通州,196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从事核试验诊断的核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创造性地解决了核爆裂变威力在严重分凝条件下的测试技术难题;创建了武器钚在较深燃耗时的诊断技术和方法;创立了地下试验中子剂量的诊断方法及解决了在铀本底严重干扰情况下放射化学诊断学的取样系数技术难题,为我国核武器的发展、为核爆诊断学的建立和完善做出了重大贡献。领导并完成了铀氢锆脉冲反应堆工程建设工作。2001年12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陈达院士轻轻搁下电话。又是记者预约采访。最近,他似乎成了新闻人物。因为,他是中国著名的核专家。
自从1945年,两朵蘑菇云升腾于日本上空之后,“核”,便成为最容易牵动国际社会敏感神经的字眼。60多年后的今天,在铺天盖地的各式新闻之中,伊朗核问题、朝鲜核问题,依然那样的抢眼、夺目,时不时让我们悚然一惊。
当争议在全球的每个角落响起时,古老的南京,竟然也有不可思议的回声。陈达,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生导师,于是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常常成为记者们追逐的对象。
然而,又恰恰因为“核”的神秘与特殊,他几乎从不接受记者的采访。这些我都知道,但我不肯放弃。
终于有一天,朋友在电话中告诉我:“明天上午8点半,陈院士在办公室等你。”

考上清华,父亲却让他去学钳工
朝鲜进行核试爆之后,人们最为关心的是这次的爆炸威力有多大?真是核爆炸么?他们的核能力究竟有多大?如何判断这些,在核科学里有个专门的学科,叫“核爆诊断学”。陈达院士便是中国为建立和完善这门学科做出重大贡献的人。
陈达跨入核科学这个神秘的大门,是在50年前。那年,他20岁。
“1957年,我考进清华大学。”接到录取通知书后,陈达却在默默整理去上海一家工厂的行装。因为无法凑齐120元的学费,父亲让姑妈在上海联系了一家工厂,让陈达去学徒,学做“外国铜匠”,也就是钳工。母亲知道儿子的心,可也只能在一旁悄悄抹泪。
“家里一直很穷,可算是赤贫。我1937年出生在南通的东社镇,日本人打过来的时候,我们一家躲到了乡下。等回来,日本人放火烧了半条街。我家的房子被烧成一堆瓦砾。什么吃的也没有,一家人到处去挖野菜。实在饿得不行,就挖点芦根,芦根是甜的,用它泡水喝。”
“最难的日子熬了过来。父亲靠卖麻团、油条养家糊口。上小学时,正值国共双方在家乡附近拉锯战,我的学习因此时断时续。课本买不起,小学老师帮我买,其实当时他们的工资也少得可怜。我没有笔和纸,就用毛笔蘸着水在砖头上练习。晚上,土霉素瓶子做的小油灯,是父亲做活要用的,我只能到家境稍好的人家去看书。我能读完高中,父亲已经尽了全力。”
1957年那个炎热的夏天,距离开学的日子只剩下两天。陈达绝望地沿着家门口的小路漫无目的地向前。不小心,竟一头朝迎面而来的自行车撞去。骑自行车的是他的小学老师曹锦琪。曹老师给了他35元。学费够了。
“进了清华,就好了。”在陈达就读清华大学的这几年里,是国家最为困难之时。然而即使是三年自然灾害,即使全国有无数的人死于饥饿,国家依然竭尽全力,保证学生们的粮食供应。年轻而贫瘠的共和国,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教育,寄托在未来。
“我在清华读书时,能减免的费用学校减免了,不能减免的,全靠国家的助学金。国家承担了一切,我只要专心学习。”
1963年毕业分配时,陈达填写的三个志愿都是到边远地区去。他可以填五个志愿,其中有一个志愿是“是否愿意留校”,他空着,没填。“是否服从分配”,他还是空着。因为他的成绩优异,先是老师找他,问他为什么不填留校,陈达支吾过去。接着,系主任亲自找他,他依然不置一言。
“在当时,就有‘金北京,银上海’的说法。很多人都想留在大城市。大城市的生活条件肯定是要好些,可我学的是核科学,我就应该到搞核研究的地方去,边远不边远,无所谓了。另外,我完全是国家培养出来的,我不去最艰苦的地方,谁去?”
26岁,正是青春年少风华正茂,陈达一头扎进大西北茫茫的戈壁滩,这一去,就是30多年,等他再次回到城市,已是两鬓霜白的老人了。

原子弹爆炸,他去采摘那朵蘑菇云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声惊动了整个世界。这一天,法国总理(后任法国总统)蓬皮杜在他的日记中写道:现在,是人们讨论中国重返联合国的时候了。
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尖端人才,愿意终身隐姓埋名,甚至以付出生命为代价默默无闻地工作;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尖端人才,甚至要忍饥挨饿,双腿浮肿地进行工作。可是,在中国大西北的荒原上,却不可思议地聚集着一大批这样的中国人。他们不仅是中国的精英,也是世界范围内最杰出的科学家。就是这些个不可思议,为自己的祖国,创造着在外部世界看来,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奇迹。
直到今天,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已经离开了人世,而他们的名字,却依然不为人所知。似乎因为年轻时代,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工作,回首三十年寂寞、艰苦甚至危险的工作,陈达竟然觉得自己很是幸运。
1964年,早在原子弹爆炸的4个月之前,陈达就和一大批年轻的同事们住进茫茫的戈壁滩了。
“帐篷很小,6个人挤在一起。白天地表的温度超过72℃,夜里的大风却把帐篷刮得要飘起来。去野外作业时就带两个馒头,几根香肠,还有一壶水。水根本就不够喝,就从那个用来给卡车加水的水桶里喝,一喝一口铁锈,吐了再喝。水是从几十公里外的孔雀河里运过来的,因为水里饱含镁离子,喝了就拉肚。就是这个条件,可是没有一个人叫苦,彼此之间也没有任何的口角,特别地团结。不只我们这一组,当时的人,都是这样。”
时间极其的紧迫,他们几乎顾不上休息。他们此时的任务是选择原子弹爆炸后,采集样本的地点。一天要跑很多的地方。中午实在太累太热,就躲在卡车的车厢下面稍作休息。
这仅仅是工作的一小部分。陈达他们这一组的任务是采集原子弹爆炸后的灰烬,并对灰烬发生的变化进行分析。采集灰烬的工作,并不像我们想象得那样简单。专家们必须事先设计好详尽周密的方案。在什么地方取样?在什么时机取样?不能有丝毫的误差。时间早了,核辐射会带来致命的危险;时间晚了,又会失去数据的准确性。而如果无法得到准确的数据,就不知道这次试验的结果到底如何。也就不能为以后的试验,提供有价值的参考。而在当时,这门核爆诊断学,对于陈达他们来说,还是一门全新的学科,很多方向上都没有人带领,只能自己一边学习,一边摸索,一边攻关。
“地面取样相对容易一点。事先确立好地点,在原子弹爆炸后,取出灰烬。而在空中取样就相对复杂了。因为那必须在蘑菇云腾空之后,就那么短的时间内,对飘浮在空中的蘑菇云的颗粒进行不同层面的采样。选择什么时机,用什么方式,这是我们事先要反复计算的,来不得半点差错。”
取到样本之后,更为复杂艰巨的任务又在前面等着他们。
样本的分析才是最重要的。原子弹的爆炸能量到底有多大?效果如何?全要看分析后的数据。而且,这些数据将会为下一次爆炸的改进或者核武器的更新,提供依据。可是,从计算数据的方式方法,到计算数据的工具仪器,再到研究的方向、门类,几乎每一个项目都是新的,都得自己摸索。而且绝无退路,只能成功,不许失败。
“1970年的那一次,研究一种材料的燃耗测试技术,我有半年多的时间没睡过一次安稳觉。常常是刚躺下来,有想法了,马上就爬起来。累了,倒下来睡一会儿,一醒,用冷水洗把脸,继续做。”
而他,就靠一把计算尺,一台手摇计算机,半年之后,硬是做出了完美方案。
然而,也正因为这种被迫的攻关,培养出了陈达极强的攻关能力,也一次次地加强了他攻关的勇气和信心。利剑总是在磨砺中,才显出锋芒。年轻的中国,摆在陈达他们面前的,有着太多的等待他们前去开垦的土地。在陈达进入核领域工作后七八年时间里,他的科研工作变动有7次。每一次,都是进入一个空白,建立一个新的实验室。每次虽然都是一次挑战,不过,同时,也是一种诱惑。
“起先的10年,是学习,是积累。后来的10年,认识开始深化,能够主动提出一些有新意的东西。接下来的10年,在自己领域内,才找到一点自如的感觉。能够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了。”
这就是陈达荒漠中的30年。“每年的蔬菜就是三大样:萝卜、白菜和土豆。土豆常常发芽了,削掉,再吃。主食就是苞米糊糊、窝窝头。”
“不过,现在的条件好多了。都是几代人建造出来的。现在再去,要吃蔬菜,直接从温室里采下来,鲜得很,比内地的还好。”陈院士笑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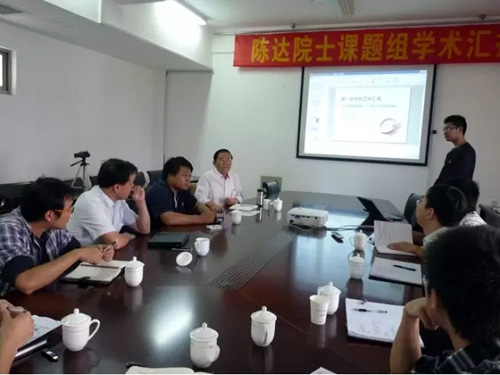
从核武器,他转向核医学研究
陈达的大半生都在进行核武器的科学研究,饶有意味的是,在他60多岁后,却将核医学研究作为最重要的目标。核,既是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也是救人于苦难的医学技术,陈达的选择,看似是对自己过去的反驳,实则是年轻时理想的延伸。对于中国科学家而言,核研究,从来不是为了伤人,而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国家和人民,而现在,陈达更希望他的研究,能够造福全人类。
2001年5月,陈达先生从西安核技术研究所来到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我一生都是在从事核科研工作,现在的年龄,说实话,有了积淀,也有了更多的相对成熟的想法,也更能发挥自己的能力与长处。”
陈先生初到南航便创建了核医学物理系。从核武器的研究,转为面向治疗癌症的核医学研究。
2001年12月,陈达先生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陈院士坦言,现在摆在他面前的核医学之路,困难重重。他曾经和中科院6名院士、10多名专家联名上书国务院,希望推行医学物理师制度。
“在发达国家,医院里已经设有医学物理师的岗位。这对诊断准确性和癌症的治愈率都将有很大的提高。现代医疗水平,不仅显现于传统人体医学的进步,更是医学物理、图像、信息等高端产品等理化知识学科交叉运用的集中反映。”
事实上,核治疗技术我们并不陌生。用于治疗癌症的放疗方法,就是一种核治疗方法。
“我们用放射线来杀死癌肿瘤,肿瘤的形状、大小,是不规则的,我们利用核技术,给它定型,锁定它。肿瘤周围的癌细胞较容易杀死,而杀死中间的要困难些,必须加强剂量。由此,放射线必须适时调整。我们为此开设的学科叫做‘适形调强治疗’。”
“我们所进行研究的目的,就是加强放疗效果,增大癌症的治愈率。对于核医学中的射线粒子而言,肿瘤是个空空荡荡的容器。射线往往会和癌细胞擦肩而过,不容易射准。人体中绝大部分都是水分子。所以,射线击中的,往往会是水分子,这时就会产生一种自由基。而这就会给人体带来很大的副作用。另外,射线从人体外射入时,必须通过健康的躯体,才能到达肿瘤,这中间,也会给人体带来副作用。所以,我们的研究,就是如何加强诊断的准确性,减少副作用,增加医疗效果。”
目前,陈院士的主要精力,就在为核医学学科搭建平台,开辟新的教学领域。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在他的努力下,目前已经建立了全国第一个“核医学物理系”。而做这些工作,虽然意义深远,可是由于种种原因,并不能在短时间之内体现出价值。对此,陈院士既深感忧虑,又极富信心。
“虽然在学科的建立、医院设立医学物理师岗位等方面进展缓慢,但在科学家们的推动和呼吁下,比如在高端的仪器研发方面,已经有部门对此开始关注。这是一门关怀人类的科学,是为民谋福祉的事业,一定要有人去做。”

采访结束,70岁的陈达院士骑着自行车,投入到人来车往中。这是和平时期的正午,阳光给街道打上了温暖的底色。脚步匆匆的人们,大多数是成为生命链条中的一环,赡养老人、养育孩子,他们为社会工作,并且获取自己的所需。而只有少部分人,会为文明的推进,起到不容替代的作用。他们的付出与取得,则是无法估量的惊人的落差。陈达说:“对于得失,个人不应看得太重计较太多。世界上没有绝对公平合理,人类还没有发明功德天平,能准确衡量出某人的功劳占百分之几。合理是相对的。”所以,陈达与平常擦肩而过的每个人一样,平静而怡然。唯一能让他激动的是:他的科学研究,究竟如何才能尽快运用到造福人类的事业中。
这,是科学家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