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六十载 报恩母校情
2020年年末,筹建两年多的清华大学科学博物馆收到了一份“厚礼”—— 古生物化石与标本、欧美老相机、明清衡器与近现代度器4个门类共34件科学类藏品。
成立时间并不长的清华大学科学博物馆此刻能收到这样一批捐赠,对于充实馆藏无疑有着积极意义。而捐赠背后更为触动人心的,则是此次捐赠的主人公、清华大学土木建筑系58级校友、清华大学顾问教授王纲怀一段长达60余年的拳拳学子情。

王纲怀先生
事实上,无偿捐赠藏品助力母校的博物馆建设,对于王纲怀而言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2011年4月,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前,他捐赠了中国铜镜和日本铜镜各100面;2016年,他再次向母校捐赠73面铜镜;同年9月,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开馆,他的“贺礼”是自己珍藏的西汉中期“必忠必信”铭草叶镜。此外,作为土生土长的上海人,2019年他还向复旦大学捐赠铜镜118面。
当外界为王纲怀的慷慨出手惊叹时,或许还不曾意识到,比起捐赠数量,这位痴迷铜镜超30年的藏家真正令人钦佩之处,在于孜孜不倦的研究和乐于分享的情怀——这些年来,他发表研究论文120余篇,出版有《三槐堂藏镜》《唐代铜镜与唐诗》《日本蓬莱纹铜镜研究》《止水文集》和《铜镜断代十讲》等近30部研究专著;他认为藏家应该有传承文明的胸怀和格局,希望有更多人尤其是年轻的学子,能在一代人所打下的基础之上,继续去探寻文物的内涵……日前,在清华园,本刊记者见到了这位被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李学勤评价为“近年来铜镜研究领域中成果非常卓著”的资深藏家,《中国收藏》杂志也有幸成为他第一次正式接受专访的媒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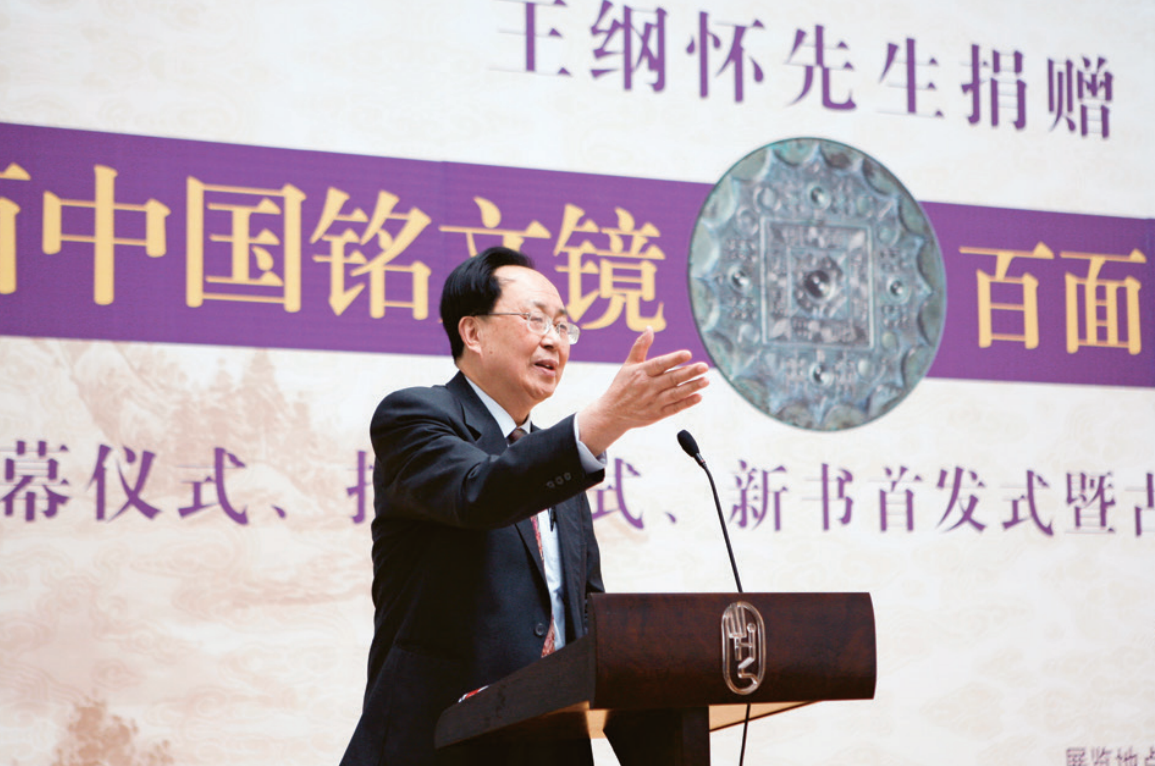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多次举办王纲怀捐赠铜镜展,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称赞

图为王纲怀与家人一起出席展览开幕仪式
说捐赠:魂牵梦萦一世缘
1958年,16岁的王纲怀走进清华大学,在土建系给排水专业学习。60多年后的今天,当他每每漫步于清华园,总是感慨不已:“魂牵梦萦清华园,母校学子一世缘。毕业这么多年了,这是我经常会在梦中见到的场景。”
《中国收藏》:在您看来,就读清华大学带给您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王纲怀:在清华,不只是学专业知识,还要学做人,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培养社会能力等,这使得我们成为全面发展的人。而最重要的熏陶,应该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校训的精神濡染,这对我来说是一种终生受用的财富。
《中国收藏》:正因如此,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时您决定捐赠藏品?
王纲怀:是的。2009年,为筹备母校百年校庆,清华大学校友总会寄来了筹建艺术博物馆的方案及图纸,李学勤老师又力邀我返校,参加“清华简”正式入藏后的第一次专家研讨会。当时我就想,“老妈”过百岁华诞,做“儿子”的总得要孝敬些什么。2010年到北京,我决定向母校捐赠铜镜100面以示祝贺。到校后,又喜闻清华大学日本研究所成立,于是又决定将我收藏的100面日本和镜一并捐赠。
清华大学领导对此十分重视,专门安排两辆专车和十余位随行人员来上海我居住的小区接“宝贝”。出发的那天早上,我翻出读大学时自己手刻的红双喜字,贴在每一个箱子上。对我来说,这可不就是“女儿出嫁”嘛。临出发时我又想,既然“嫁女”,能不能既放个鞭炮,又不会打搅邻居呢?于是就建议“我们一起学个放鞭炮的声音吧。来,砰——啪!”在这种喜庆的氛围中,我完成了一个心愿,也算是对母校培育之恩的努力回报吧。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常务副馆长杜鹏飞为王纲怀颁发捐赠证书
《中国收藏》:向清华大学科学博物馆捐赠又是因为何种契机?
王纲怀:2019年4月,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就我捐赠的日本和镜,举办“扶桑止水铜镜展”。参加开幕式的时候,我注意到,在艺术博物馆南边的美术学院一楼展厅,“百年器象——清华大学科学博物馆筹备展”也在同时进行,而且是首展。我意识到,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是社会进步的两翼,不可分割。母校办这两个馆的初衷,就是要把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融合起来,培养新时代的大学生。我感觉,既然对艺术博物馆有捐赠,科学博物馆也不可或缺,我有义务为母校建一流学校、育一流人才再助绵薄之力。加之我年轻时爱好摄影和收藏,这方面也有一定的藏品,所以回上海后,整理出4个门类共34件科学类藏品,在去年底完成了捐赠。


王纲怀捐赠给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的西汉中期“必忠必信”铭草叶镜拓片,以及捐赠给清华大学科学博物馆的古董相机
说收藏:汉碑引领走进铜镜世界
1979年,王纲怀调至上海环保局,担任黄浦江污染治理总体规划负责人。1982年,他又调入新组建的上海市国土整治办公室。1984年开始,他执笔撰写并发表论文《上海的曼哈顿区在哪里?——结合城市改造在外滩建设新的金融贸易中心》、《上海的特区在哪里?——结合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在外高桥建设经济特区》。这些文章得到了领导部门的重视,不久即在上海市政府委托的“上海城市发展方向”课题中,担任了总负责人并兼浦东方向分课题负责人,完成了《浦东新区建设方略》。随着改革开放的号角响起,他和同事们一道,围绕着上海旧城改造、新区建设、浦东开发等专题,进行了长期深入的探索。
熟悉王纲怀的人都知道,他对工作相当严谨,办事的时候,时间把握很精确。然而,在生活中,尤其沉浸在艺术收藏世界时,他又是另一种悠然的状态。

专业、严谨、科学,这是王纲怀做事的一贯风格。所以,对于捐赠藏品,他和博物馆团队都要经过认真研究,再一一编号
《中国收藏》:听说您爱好收藏是受家族的影响?
王纲怀:对!《三希堂法帖》中的《伯远帖》作者王珣,是我这个王家的直系祖先,所以家族血液里就带有爱好艺术的因子。我的伯父王纪泽在邮票界被称为“红印花大王”,可算是一领域的“泰斗”级人物。受长辈影响,很早我就开始集邮,是上海集邮协会的第一批会员。后来我觉得集邮不过瘾,兴趣又转到了收集古代钱币。
因为喜欢书法,练帖接触汉碑隶书,为它的方拙、典雅、奇古深深吸引。1992年,我在上海古玩市场偶然看到一块铜镜残片,被铭文的汉碑字体所折服 ,简直有一种顶礼膜拜的感觉,从此开启了铜镜收藏之旅。2000年元旦我正式退休,也就有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收藏和研究中。

观众在展厅被王纲怀捐赠藏品深深吸引
《中国收藏》:入门之初有没有“交过学费”?
王纲怀:当然了,最开始“交学费”是一定的。上世纪80年代,我的工资不高,有一天在市场看到一块唐代骑马狩猎镜,由于之前看过相关的资料图片,很自信地以高价买了下来。但是经有关专家鉴定确认为赝品。这是我至今最大的教训。
《中国收藏》:您如何评价当年的收藏市场?
王纲怀:虽然“交学费”在所难免,但不得不说,那个时代的市场真是太诱人、太可爱了。“文革”结束,改革开放。中国进入新时期,文物市场自然也随之繁荣。
我国历史悠久,文化厚重,文物丰富。在上海,我是福佑路、东台路和会稽路古玩市场的常客;潘家园也是每次赴京必去之地;西安的八仙庵、洛阳的老集古玩市场也很诱人。在收藏铜镜的第一个十年里,我就在这些地方享受到了改革开放的红利。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我在旧货古玩市场,随着熙熙攘攘的人群,欣赏,学习,也偶尔打开并不充实的荷包淘一两件宝贝。古玩市场就是一个大学,那时的“逛”就是吸纳积累,为我日后的收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展厅现场为观众做讲解,乐于分享是王纲怀的收藏宗旨之一
《中国收藏》:回到研究上,我们注意到,这些年您的成果颇丰,比如提出关于铜镜单位面积的平均重量m值的新概念,为古铜镜的量化研究提供了新视角。最近还会有新的研究计划吗?
王纲怀:镜铭文字中,篆、隶、楷、行、草五体齐全,与石碑、简牍、帛书的书法艺术相比,镜铭文字的魅力毫不逊色。当年,一面西汉景帝时期的鸟虫篆铭彩绘镜中的鸟虫篆书体铭文,标注了铜镜铭文史的光辉起点,也开启了我对铜镜中“中国书法史”的求索之路。
铜镜里有历史密码、宇宙天道;有时光痕迹,也有绝美文化。不单是铭文,铜镜的造型、工艺、图案、纹饰等都是我想要穷尽研究的内容。在我看来,铜镜是“理性认知和浪漫思维的完美结合”。收藏铜镜这么多年,特别是退休后,我日常生活的时间几乎都花在铜镜的收藏和研究上了。为藏品寻找到一个更好的归宿,去发挥它们的文化和社会价值,我觉得更加值得。

热心地为参观者讲述展品背后的故事。对王纲怀而言,铜镜内涵博大精深,蕴藏着深厚的历史与文化
忆师友:真实真诚如当初少年
采访中,当王纲怀毫无隐讳地给我们讲起这些入行经历、经验和趣事时,很自然地就会被他的真实和真诚所感染。而今,我们眼前的他早已是业界公认的重量级人物,然而,当话题从自己的收藏延伸到与王世襄等一些前辈大家的交往时,他的语气随之变得谦恭虚己,依稀让人再次看到了多年前清华园中那位16岁少年的身影。
《中国收藏》:因为收藏与研究,您与不少大家都打过交道,他们留给您印象深刻的是哪些?
王纲怀:在我收藏的第二个十年开始至今,尤其是当我的收藏有了一定规模时,我有幸遇到了谢辰生、吴良镛、李学勤、王世襄、史树青、罗哲文、陈佩芬、辛冠洁、傅举有等前辈与导师,并且得到了他们的大力帮助与提携——有的题签、有的赐序、有的点拨、有的释疑,给近30本拙著铺上了厚重的“红地毯”。李学勤老师在拙著《清华铭文镜》序言中肯定:“铜镜研究有本身的特点,已经有条件成为一个特定的分支。”他为拙著5次赐序、1次题签。罗哲文老师为拙著《日本蓬莱纹铜镜研究》作序,鼓励我“知难而进,独辟蹊径”。这些都使我终生难忘!

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李学勤先生(图右)评价王纲怀为“近年来铜镜研究领域中成果非常卓著”的资深藏家。他曾为王纲怀著作5次赐序、1次题签,实可谓良师益友。
《中国收藏》:您和王世襄先生的交道又是如何开始的呢?
王纲怀:我与王世襄先生开始交往是在2007年。那年他看到了我的《唐代铜镜与唐诗》书稿时,就向有关方面打听,托口信让我联系他,有空去他家一趟。
先生是大家,如约晤面时,我既兴奋又忐忑。他寒暄致意,让座倒茶,随性适意,使我有一见如故之感。先生当时主要跟我谈《唐代铜镜与唐诗》这本书,要我说说是怎么想到这个题目、怎么个思路写作的?我详细谈了著述的前前后后,他听得很专注。当时我说到“借用一个材料工程学上的比喻,一个大的社会就像一台大的设备仪器,唐镜是物质硬件,唐诗是灵魂软件,我试图把硬件和软件搓合在一起,想看看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先生点头称赞:“明白了,全在里头了。硬件和软件串起来,实物和文化连起来,价值就大幅提升,效果就大不一样。《唐代铜镜与唐诗》这本书大有启发。”
听到先生的鼓励,我已经很高兴了,接着他又说:“听说《唐代铜镜与唐诗》修订再版,而且还有几本书的出版计划,你想让我题签?可以的,就将书名一起给我吧。”这简直令我受宠若惊,连声道谢。果然,不久后,先生题写的《诗辉镜耀(唐代铜镜与唐诗)》墨迹就寄到我家。后来先生又为拙著题写了《镜铭书法(汉铭斋藏镜)》、《历代镜铭考略(清华铭文镜)》。王世襄先生虽然离世了,但睹物思人,我一直铭记他的教诲,把他的鼓励和提携当作自己前行的动力。

著名文物专家、学者、文物鉴赏家、收藏家王世襄先生为王纲怀著作多次题字。虽然先生离世了,但睹物思人,王纲怀一直铭记他的教诲,把他的鼓励和提携当作自己前行的动力
《中国收藏》:之后您跟王老还有过往来吗?
王纲怀:后来,先生让我帮他找一找关于驯鹰的唐诗。回到上海后,我花了几天时间整理好,给先生寄了过去。可是由于他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其著述未能面世,这也是我至今深为遗憾的事情。
而最让我“有成就感”的一件事,就是促成了王世襄老先生和辛冠洁老先生的认识。辛老是抗战时期《大众日报》总编辑,从事新闻、外事等工作多年,晚年离休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与王老一样,他也喜欢收藏葫芦,并且水平很高。当时北京城玩葫芦能排上号的只有那么屈指可数的几个,因此他俩认识后,都很高兴。我想,这种感觉大概就是志同道合、相见恨晚吧。
《中国收藏》:您曾说过,向复旦大学捐赠,是完成对师友的承诺。
王纲怀:没错,这是我对上海博物馆原副馆长陈佩芬的一个承诺。2008年,因为修订《唐代铜镜与唐诗》一书,我曾多次向陈馆长求教,由此彼此逐渐熟络,有时候她还会邀请我一起去看民间收藏的铜镜。她曾嘱咐我,复旦大学博物馆铜镜收藏薄弱,将来如有可能,一定要多支持。2019年10月先生逝世6周年之际,完成此事也是我对她的一种纪念与告慰。
《中国收藏》:说到志同道合的朋友,您最大的感触又是什么?
王纲怀:一个人的成长离不开周边环境,我在收藏上所取得的每一个进步,除了“身逢其时”外,也完全离不开朋友们的扶持。比如周志豪、徐也力、孙小龙等藏友,大家经常会聚在一起交流、切磋、研讨。互相支持对于我们好友而言也是常事,台北大藏家陈灿堂先生,在实物与资料上都曾给予我鼎力相助。
艺术无国界,对此我有过真切的体会。我去日本京都泉屋博古馆参观的时候,馆长樋口隆康前辈亲自陪同并细心讲解。多年来,我们之间互有书信来往,交流研究心得。2012年,年逾九旬的樋口先生来函,要我帮助释读奈良东大寺法华堂修缮时所发现的一面铜镜铭文,我历经数月,查找资料,终得答案,并予回复。为纪念此事,有拙文《诗辉镜耀》发表在贵刊2013年第3期。

在与日本青铜器、铜镜研究大家樋口隆康先生交往的八年多时间里,王纲怀留下了诸多珍贵记忆。在晤面交谈与书信往来中,两人探讨过中国早期铜镜等有关问题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冈村秀典教授先后4次来我家借拙藏铜镜做拓片,他曾受邀参加清华大学《汉镜文化研究》课题活动,提供了论文《汉镜分期研究》。在我去京都大学图书馆寻查资料时,他也为我提供了尽可能的方便。
一个好汉三个帮,再有就是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博物馆一批年轻有为的学者倪葭、安夙、高文静、高宁、麻赛萍、李新城、邱龙升、沈依嘉等,他们在历史、文字、文学和文物保护等领域都有卓越的成绩,同样给了我不少帮助与支持。后生可畏,这也是让我乐于见到和深感欣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