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2月,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由长沙迁昆明,开始了一次“长征”,由此所产生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已经成为了在中国现代教育史和文化史,乃至全世界高等教育史上的一段传奇,广为传颂。“2月19日至4月28日,三校两百余名师生组成‘湘黔滇步行团’,在闻一多……等教授的带领下,步行三千五百华里,历时六十八天,跨越湘、黔、滇三省而抵达昆明。查良铮以‘11级清华学号2720(外)’编入12级学生为主的第二大队一中队一分队……”近二十年前,我作为一个新诗入门学生,第一次读到李方先生所编的《穆旦(查良铮)年谱》(“简编”收入《穆旦诗全集》,增订版现收入《穆旦诗文集》,该年谱对穆旦研究的助益和推动之功无需多言)中这段文字时,印象特别深刻,今天重新翻阅,仍感到心头一震。

穆旦(查良铮),1918-1977。

《穆旦诗全集》
查良铮出生于1918年,1977年辞世时,年仅五十九岁。今天,在纪念这位伟大诗人和翻译家诞辰百周年之际,我想和大家一起回到查良铮还不是“穆旦”(虽然他已经发表过诗作,但所用笔名还是“慕旦”)的那个时刻,回到他作为清华外文系学生参加步行团的那个时刻。那时,“炮火翻动了整个天地,抖动了人群的组合”(卞之琳语),整个中国都呈现出战时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流动性,世界也在经历着地图的大变动:内迁、南渡、归来、流亡、困守孤岛、到延安去、下乡入伍、远赴南洋……同样在1938年,中国现代诗人卞之琳内迁至成都后,又开始前往延安的访问,而英国现代诗人奥登则前来中国战区采访,在我以前的一篇文论中,我将这两次诗歌的流动和穆旦等西南联大文学青年的行程并置,称之为“抗战时期现代主义诗歌的三条路线”。穆旦一生充满传奇也饱经苦难的旅程,正开始于学生时代的战时迁徙。也许我们可以在战时文学的地缘政治中,乃至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经验的流动版图中寻找其人其诗的另一重定位。

查良铮,1938年5月摄于从长沙步行到昆明之后。
查良铮的抗战经历使得他成为了新诗史上的穆旦。要讲述诗人和诗歌的“出发”,则要从三校逗留湖南说起。华北失守,北方许多大学开始逃亡;其中,北大、清华和南开迁至长沙时成立了长沙临时大学,1937年11月1日开始新学期。英国诗人兼批评家燕卜荪(William Empson)作为清华的教授,随部分文科被安顿在了南岳衡山附近。在衡山,他写下了他一生中最后一首长诗——《南岳山中》。这首诗是围绕一个词展开的:flight。它既指飞行,又包含了“逃” (flee)的意思。全诗结束于诗人对进一步逃亡的不确定感:“I said I wouldn’t fly again/For quite a bit.I did not know…”并把抗战、临时大学的搬迁和南岳自然景象转化为一种对流动性、不确定性的表达:“Thesoldiers will come here and train./ The streams will chatter as they flow.”燕卜荪对一个词的关注折射出了他“和流亡大学在一起”的中国经验。可惜这首诗当时被《生活与文字》(Life and Letters)退稿,而同一个刊物多年后发表了王佐良介绍穆旦的文章。1938年2月,日军进犯,湖南吃紧,临时大学再次搬迁。对于那些步行团的学生来说,逃亡恰是“飞行”的反面,那意味着深入中国的内陆,深入土地。“澄碧的沅江滔滔地注进了祖国的心脏……”(穆旦:《出发》,《穆旦诗文集》卷一,205页)。这是穆旦纪念这段“三千里步行”穿越湘黔滇的经历时所写的第一句。远离“渔网似的城市”,接触“广大的中国人民”,已经预示了这一代新诗人和三十年代诗风的距离。“我们不能抗拒/那曾在无数代祖先心中燃烧着的希望。”(穆旦:《原野上走路》,同上书,208页)战时的流动性重新组织了文学青年的社会经验和生命体验,使他们深入到以前新文化无法触及的区域。与此同时,燕卜荪作为清华教授则“飞行”出了一条曲线,他先去香港,肩负为联大采购物资的任务,在这片殖民地上碰见了同胞奥登,对这位“战地诗人”似有不屑,然后又取道法属越南辗转来到了云南。很快,查良铮就会出现在他的英语诗歌讲堂中。又没过多久,从延安归来的卞之琳也加入了联大教授的行列,而作为学生辈的穆旦,后来在书评中批评了卞之琳的战地摄影般的诗作,反而赞赏艾青的凝重激烈的油画般的北国风景书写,提倡“健美的抒情”。也许,早在穆旦的徒步远行中,民族解放的政治意识、新的抒情可能性和历史视野已初步成形。

燕卜荪
王佐良,作为穆旦的同学,既是西南联大诗歌生活的亲历者,又是穆旦的最重要的评介者之一。在他从四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多篇文章中,王佐良都追述了穆旦诗歌养成的两方面。一方面,王佐良提及了“三千里步行”对他诗风变化的影响:“他是从长沙步行到昆明的,看到了中国内地的真相……他的诗里有了一点泥土气,语言也硬朗起来。”(《穆旦的由来和归宿》)还有:“……抗战爆发,他的情绪高扬了,但由于他在流亡途中看到内地农民受苦的样子,又是常有忧郁的反思的。”(《谈穆旦的诗》)另一方面,王佐良也强调穆旦在到达昆明后所受的现代主义教育,在燕卜荪对从霍普金斯到奥登的英语现代诗歌的讲授中,穆旦进入了现代主义诗歌的世界,成为了“年青的昆明的一群”中最为耀眼的诗人。抗战的社会流动性和大学的流亡形成了一个新诗歌群体及其集体经验:“这些脸大的年青诗人们并没有白读艾略特和奥登……这些年青作家迫切地热烈地讨论着技术的细节,高声的辩论有时深入夜晚;那时候,他们离开小茶馆,而围着校园一圈又一圈地激动地无休止地走着。”(《一个中国诗人》)

王佐良,西南联大毕业留念,1939年。
至少在穆旦的个案中,四十年代新诗的国际现代主义的脉络显得特别清晰,因而也得到了相当多的阐发甚至引发过一系列争议。不过,其背后的战时本土经验也不应遭到淡忘。关于“三千里步行”,穆旦有过两首诗作:《出发——三千里步行之一》《原野上走路——三千里步行之二》。这两首诗写作时间一般推测是步行长征期间或随后,发表则是1940年,它们没有被收入穆旦自己编订的任何诗集,或许有习作痕迹较重的原因在。不过,有意思的是,当年的带队老师闻一多后来把《出发》这一首收入了《现代诗抄》。放在穆旦的整个诗歌历程之中,也可以将这两首诗作为他的写作在“奥登风”之前的另一原点,一个历史经验的原点。除了我已经引到的开头之外,《出发》一首以内陆地名的排比来建构对“中国”和“人民”的新感知:
在军山铺,孩子们坐在阴暗的高门槛上
晒着太阳,从来不想起他们的命运……
在太子庙,枯瘦的黄牛泛起泥土和粪香,
背上飞过双蝴蝶躲进了开花的菜田……
在石门桥,在桃源,在郑家驿,在毛家溪……
我们宿营地里住着广大的中国的人民,
在一个节日里,他们流着汗挣扎,繁殖!(《穆旦诗文集》卷一,206页)
在《原野上走路》中,诗人强调了“我们总是以同一的进行的节奏,/把脚掌拍打着松软赤红的泥土”;“中国的道路又是多么自由而辽远呵……”(207、208页)穆旦四十年代的许多其他作品已经成为了中国现代主义的经典,和它们相比,这些行路“中国”的诗行或许缺少那种“玄学、身体、历史”相互扭结的标志性强度,但今天回看,这两首诗作具有另一重意义上的特殊价值,它们是“中国”之为现代国族在战时流动和重构的文学印痕。

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朱自清、罗庸、罗常培、闻一多、王力。
而且,穆旦的旅程并没有就此结束。到了1942年2月,穆旦作为翻译随远征军进入缅甸战场,5月至9月经历大撤退,九死一生从胡康河谷的热带森林逃至印度。这些联大“学生兵”中写诗的并不只有穆旦。杜运燮的《滇缅公路》记录了新的交通线的艰难铺设,穆旦事后谈到了原始森林“殿后战”中的“对大地的惧怕”。他们积极参与到新战场的开辟之中,也改变了现代诗的版图。这两位从滇缅战区归来的诗人最终参与到了“中国新诗”派(也称为九叶派)的“新诗现代化”的实践,“野人谷”之战中幸存下来的诗人已经被公认为是中国新诗史上最为重要的诗人之一,只不过那段直面死亡的旅程,作为他的诗歌的又一个源头,也许永远留在了原始森林。王佐良等人都提到过,活下来的穆旦并不怎么和人说起那段经历。关于野人谷,穆旦只留下了一首以诗剧为形式的《森林之魅——祭胡康河谷上的白骨》(1945)。该诗以“森林”和“人”作为两个寓言角色,其中“人”告诉我们:“我不和谐的旅程把一切惊动。”(《穆旦诗文集》卷一,147页)《森林之魅》作为关于远征军经历的唯一一首中国现代诗,又被唐湜称为“小史诗”。诗中“森林”代表了原始的自然力,代表了死亡和死亡冲动,而“人”代表了旅程和文明。诗人最后唱出了关于人类文明、死亡和历史的“祭歌”:
过去的是你们对死的抗争,
你们死去为了要活的人们生存,
那白热的纷争还没有停止,
你们却在森林的周期内,不再听闻。
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
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
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
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同上,149页)
死亡,在具体的历史纷争中不断地沉入历史之外,但却成就了另一种无名的“滋生”。正如唐湜所指出的,“原始的自然”成为了历史斗争的归宿,“这一去而不复返的故乡就是人类历史与自然史的交点”(《搏击者穆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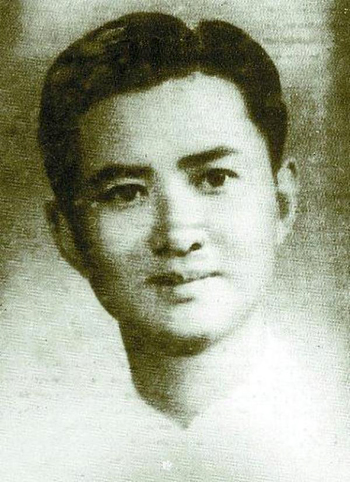
唐湜
这首诗的诗剧形式似乎和袁可嘉所看重的诗剧中的综合力有一种呼应。袁可嘉发表于1947年的《从分析到综合》指出,“分析从强烈的自我意识出发,采取现代飞行员的观点,即把个人从广大社会游离出来,置身高空,凭借理智的活动,俯视大千世界”。分析是一种鸟瞰,一种全面的反讽。相反,“综合”应是中国“新诗现代化”的方向。它不仅仅是对现代社会的攻击,而且包含着“悲愤”和“怜悯”,走向一种“错综复杂的人性的发展”。袁可嘉将“综合”定位为现代诗的“挣扎形象”:“极度个人性里有极度的社会性,极浓厚的现实主义色彩里有同样浓厚的理想主义气息。”这无形中为穆旦的战时诗歌轨迹提供了一个迟到的说明。“飞行员”是战争带给现代诗的新意象。但穆旦的历程和写作则是不断深入旷野、大地以及“肉体的诱惑和痛苦”。他反对机智而主张“有理性的”抒情。他最令人瞩目的特点是“血肉与思想的浑合”,他被定位为一个以“带电的肉体”在时间的激流中“搏击的诗人”(唐湜:《搏击者穆旦》);这和分析的、反讽的“飞行”姿态大为不同。而且,在穆旦四十年代的写作中,这种“搏击”时常指向一个深层的“未成形的黑暗”,一个原始的交点或“根”,那既是“我的形成”也是死亡,既是“终止”也是“二次的诞生”。但我以为,这种对原始的生死合一状态的冲动和“探险”(他把自己第一本诗集命名为《探险队》)直接对应着诗人深入内陆的历史经验:先是深入祖国的“红土”内陆,然后是深入亚细亚的内陆,最原始也最现代的生命体验的内陆。

袁可嘉,1947年。
在穆旦这样的四十年代诗人中,隐含着新诗和现代国族经验的新关联。朱自清当年就曾感叹过杜运燮《滇缅公路》这样的新作,它们未必成熟,却写出了古代诗歌和早期新诗都不可能触及的新经验,而这种经验是特属于正在死与生中建构着的二十世纪中国的。但是,这里就涉及到穆旦诗歌的一大争议点,那就是它的“非中国性”,不论是他的赞美者还是批评者,都曾强调过他现代主义倾向中“去中国化”的一面。王佐良最早说穆旦“最好的品质全然是非中国的”(《一个中国诗人》)。周珏良说穆旦“受西方诗传统的影像大大超过了中国旧诗词的影响”(《穆旦的诗和译诗》)。有人也由此认为,穆旦最少中国传统的影响,代表了新的诗歌感受力和语言。不过,对江弱水这样认为穆旦被错误“高估”的批评家来说,穆旦的诗作一方面构成对英美现代主义的肤浅模仿,一方面又和传统中国诗歌生活缺少联系,所以代表了无根的“非中国性”。的确,说回到《森林之魅》,诗剧对话体显然是一种相当欧化的形式。而且,这种宗教-寓意剧的形式贯穿穆旦整个诗歌生涯。《隐现》基督教气息明显,有“宣道”“历程”“自白”和“合唱”的环节。《神魔之争》中有“东风”“神”“魔”等角色。而到了穆旦晚年的《神的变形》中,“神”“魔”“人”的设定之外,又有了“权力”这一寓象。这一创作脉络全面显示出穆旦所接受的西方文学、文化影响。穆旦对英语诗歌形式的借用当然远不止于此。如果仔细观察,连书写中国内陆的《出发》也是两段十四行组成的,表现为4-4-3-3-8-6的形式构造。但这是否意味着这些诗作的“非中国性”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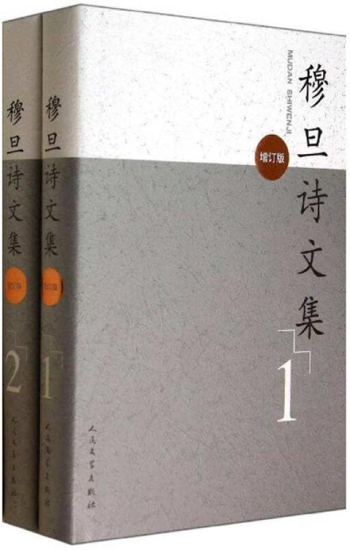
《穆旦诗文集》
同样,江弱水先生当年曾犀利地指出过穆旦对现代英语诗歌的意象和譬喻的因袭。在这方面,他所没有举到的一个例子就出现在《森林之魅》的结尾生命化入树根的意象。叶芝的诗作中,生命枯萎,随时间进入智慧之树的根。智慧之树在穆旦的诗作也反复出现,却总和爱欲、死亡相联系。《诗八首》的结尾则归于“巨树”和“老根”:
……
而赐生我们的巨树永青,
它对我们的不忍的嘲弄
(和哭泣)在合一的老根里化为平静。(《穆旦诗文集》卷一,80页)
到了建国以后,智慧之树成为了历史的强制否定性的隐喻。在被错划为“反革命”之前,穆旦曾写出过“平衡把我变成一棵树”(《我的叔父死了》)的句子。而在他的不幸晚年,他的《智慧之歌》变为沉痛的诅咒:
但唯有一棵智慧之树不凋,
我知道它以我的苦汁为营养,
它的碧绿是对我无情的嘲弄,
我诅咒它每一片叶的滋长。(《穆旦诗文集》卷一,319页)
如果说,穆旦早期对内陆的深入在诗歌中构成了从原野到爱欲到老根、死亡和原始的“合一”,那么,历史最终在他的诗歌中作为冷峻、无情的“智慧”出现,却是个人生命最后抒情抵抗的对象。到了这一步,“智慧之树”究竟是一个学习西方现代诗而产生的赝品,还是中国现代历史经验本身的修辞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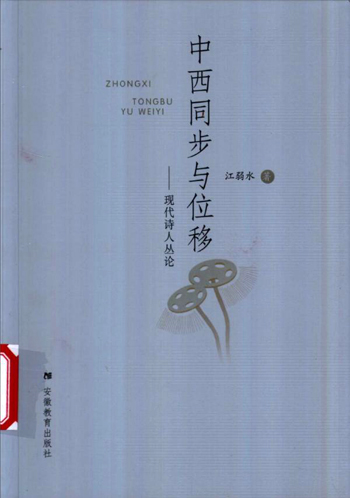
江弱水:《中西同步与位移——现代诗人丛论》,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8月出版。
2002年,江弱水先生发表《伪奥登风和非中国性:重估穆旦》,这一富于争议性的观点的确促使人们从新的角度审视穆旦。当年,作为一个学生辈,我也尝试参与相关讨论,而到了写讨论穆旦研究史的小文《重述、重读抑或重估》时才想明白,自己之所以想对“非中国性”的观点提出不同意见,并不在于什么具体文本分析上的歧异,而更多出于文化立场上的差别。中国传统诗学构成了一整个文学生活的内蕴和外延,这一稳健的、延续的、美的“中国”显然在今天也仍具有特别可贵的意义。如果把它当作诗歌“中国性”的唯一向度,那么穆旦诗作受到贬抑,也不足为奇。但这样的文化态度却难免过于排他。如此一来,“中国性”及其所有美好,就“不可能包括我在阅读穆旦时能够感同身受的那些现代中国的具体经验——那些无法命名的痛苦、欲望、虚无、反抗、嘈杂、紧张、黑暗,等等——,也不包括这种经验所具有的激烈的存在感”(拙作《重述、重读抑或重估》)。我至今仍然感觉,读穆旦那些不无“模仿”“影响”痕迹的诗作时,反而可以碰触到更实在、更不确定、更有历史质地、更具现代危机感、却也更有原动力的“中国性”。

1973年,查良铮、周与良于天津睦南道147号。
从江弱水先生的质疑文章到现在,又过去了十多年,穆旦研究早有了新的精彩发展。但我却仍绕不过去穆旦诗歌那最初的“谜”(王佐良语):他的“非中国性”却写出了二十世纪中国的“丰富和丰富的痛苦”。这个“谜”也提示,我们必须在现代文学中以更开放、更有历史辩证感的态度不断重新界定乃至充实“中国性”(而不是将某种给定的“中国性”拜物教化)。这应了另一首穆旦的集外次要作品《中国在哪里》:“因为在史前,我们得不到永恒。”“中国”和“中国性”在历史经验的含混、纠结和流动中。在此,我漫谈穆旦深入内陆之旅以及一些也许并不算经典的作品,也是希望表明,纪念穆旦就是纪念那些化入黑暗“树干”的“出发”“探险”“远征”“希望”“挣扎”“死亡”。穆旦赋予了这样的“中国性”以诗歌,用笔、用年轻的“脚掌”、用心智和血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