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贻琦先生字月涵,1931年至1948年任清华大学校长。1937年,抗日战争时,清华与北大、南开三校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梅贻琦任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翌年任西南联合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兼主席,一直到抗战胜利。《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即收录了梅贻琦先生从1941年到1946年在昆明主持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校务时期的日记(其中有间断和不少缺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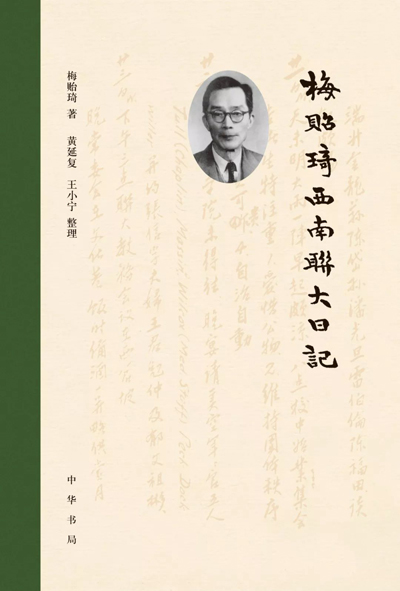
《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中华书局2018年5月
日记所记录的时间正是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八年的关键时期,跟电影《无问西东》里所呈现的场景有不少重叠之处。根据这本日记,可推断梅贻琦先生的生活有这样一些特点:第一,物价飞涨,生活紧张,不少教工兼职增加收入,而学校领导到处筹款,设法增加教职员工补助。第二,经常跑警报,生命财产没有保障,当时敌机经常来轰炸昆明,日记中有炸毁联大财产、炸死联大职工的记录。第三,校务繁重,梅贻琦先生同时掌西南联大和清华大学,事务繁重可想而知。第四,应酬频繁。为了维持联大,争取科研、教学经费,提高联大的声誉,一要和中央各部委、地方政府打交道,二是要和金融界、银行界打交道,三是要和军界打交道,四是进行国际联系,接待外国使团、学者,等等。

1946年西南联大结束后,离开昆明前梅贻琦夫妇合影
陈寅恪说过,“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吃饭读书、招待回信、说话纳凉,是最琐碎寻常的公务生活,也是民国君子的惟日孜孜、无问西东。
1941年2月7日
午前有警报,院中妇孺皆出外疏散,顿觉安静,乃至廊下坐约一时,看书晒太阳。
1941年3月22日
上午在联大办公处,至十一点出,赴梨烟村,郁文于五六日前感冒卧床,尚未痊愈,但热度已不过三十七度以内。天夕外出散步,斜阳映在远山上,红紫模糊,愈显可爱。回看村中,已在阴影,暮色苍茫,炊烟四起,坐河堤一大松树下,瞻顾留连,至天已全黑始返。
1941年6月21日
午、晚饭皆在“成都味”,有月母鸡汤、麻婆豆腐,堪称对偶。
1941年7月17日
夜半忽醒,见窗外月色正明,光辉入室,未起视,仍复睡去。4:50起床,天色微明,少顷见日出,于灰紫雾海中忽吐红轮一线,数分钟后已露四分之一,如一火轮立浮此雾海中,以后轮光渐大,立处渐远,至全轮现出,则光色由红而黄而白,而雾气消散,浮云隐现于山间天际,此时霞光犹为动人,独立户外,注视久之,惜无他人来与领略此美景也。
1941年9月14日
上午九点,赴物理学会及新中国数学会联合年会于师院附校礼堂,正之主席。演说者为赵公望。李、熊及余皆简短。余为讲学术界可以有“不合时宜”的理论及“不切实用”的研究。
1941年9月24日
晚,常委会,十点散。作信与净珊,此为回昆后第一封,恐伊必更悬念矣。
1941年10月15日
六点在西仓坡开联大常委会,郑、樊各有函请辞,讨论许久不得解决。余坚谓常委主席、总务长、事务主任不宜由一校人担任,且总务长若再以沈继任,则常委会竟是清华校务会议矣(岱孙现代序经任法商院长)。
1942年10月18日
天夕往焦山桥拜访陈善初未遇,至金碧餐厅贺何衍璿君嫁女。饭后为罗莘田约往省党部看《妙峰山》之演出,座客不多。剧本为丁西林所编,导演为孙毓棠,惜情节不够紧张,而其对话之细巧处或又非普通观客所能领会耳。
1942年12月27日
饭后至企孙处闲坐,一樵偕沈宗濂来约同至沈处看竹,因企孙在座,进行颇慢,而结果渠竟独胜。
1943年1月9日
午饭在顾家,有郝太太、郑、徐轼游及五顾,张充和女士后至,盖饭后始得消息者。饭罢某君唱朝阳校歌,后张唱《游园》一大段,佐之以舞,第恐其太累耳。
1943年3月4日
八弟处始有确息,老母竟于一月五日长逝矣!年已八旬,可谓高寿,临终似亦无大痛苦。惟五年忧烦,当为致疾之由,倘非兵祸,或能更享遐龄。惟目前战局如此,今后之一二年,其艰苦必更加甚,于今解脱,未始非老人之福,所深憾者,吾兄弟四人皆远在川、滇,未能亲侍左右,易箦之时,逝者亦或难瞑目耳,哀哉!十弟有登报代讣之提议,吾复谓无须,盖当兹乱离之世,人多救生之不暇,何暇哀死者,故近亲至友之外,皆不必通知。况处今日之境况,难言礼制,故吾于校事亦不拟请假,惟冀以工作之努力邀吾亲之灵鉴,而以告慰耳。下午五点开联大常委会,会前诸君上楼致唁,有提议会可不开者,吾因有要事待商,仍下楼主持,不敢以吾之戚戚,影响众人问题也。
1944年5月27日
午返城,四点赴民政厅讲演之约,为略讲科学在中国发达之历史及今日科学精神之亟应提倡。
1944年9月1日
晚约水泥厂厂长陈作新夫妇及茀斋夫妇、正宣、勉仲、雪屏、毓棠便饭,陈君颇善饮,共消十余斤,畅快之至。
1945年9月17日
晴热有加。午前与毅生至附近“第一泉”洗澡,尚清静,搓背、捏脚、捶腿等全套,二人共费二千二百余元,其太贵乎!
1945年10月3日
晚在朱处,饭后颇静,与珊得闲话。回忆九年结识,经许多变动,情景一一如在目前。今后经历如何,尤难测度。但彼此所想颇多,可领悟于不言中也。
1945年11月5日
饭后谈政局及校局问题颇久,至十二点始散。余对政治无深研究,于共产主义亦无大认识,但颇怀疑;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
1946年1月8日
一点余始到王家,因包饺子至二点余始午饭,携酒快饮,颇饶逸趣,韭菜包饺尤为适口,任性吞食,总在二三十之间矣。饭后看竹,获三千有零。
1946年4月26日
七点半返寓,招待各所、组教授及夫人便饭,共坐二桌,饮酒颇多,共消十二斤余。客散即就寝,稍有醉意矣。
1946年7月12日
晴。今日起始视事,中午清华校务会议,光旦迟来,始悉李公朴昨晚在学院坡被暗杀消息。下午李圣章来稍坐。
1946年7月15日
晴。日间批阅两校公事颇忙。夕五点余潘太太忽跑入告一多被枪杀、其子重伤消息,惊愕不知所谓。盖日来情形极不佳,此类事可能继李后再出现,而一多近来之行动又最有招致之可能,但一旦果竟实现;而察其当时情形,以多人围击,必欲致之于死,此何等仇恨,何等阴谋,殊使人痛惜而更为来日惧尔。急寻世昌使往闻家照料,请勉仲往警备司令部,要其注意其他同人之安全。晚因前约宴中央及中航二公司职员光徐诸君,但已无心欢畅矣。散后查、沈来寓,发急电报告教部,并与法院、警部及警察局公函。一点余始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