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馆主曰】记得去年父亲节时,馆主曾刊发丘成桐先生的大作《怀念父亲》,作为特别礼物,赠给无论身处何境的父亲们: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坚定忠厚持家,诗书传世的信念,为子孙荫翳出一片崭新天地。
转眼又到今年这一特别的日子,馆主经数学家杨乐院士的授权,特刊发他的夫人黄且圆先生所写的《纪念父亲黄万里先生》,分享给馆友们,祝父亲节快乐。
2011年8月20日,清华大学举办黄万里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座谈会。黄万里教授是清华著名的水利科学家,学养深厚,满腔家国情怀,一生致力国家水利事业,坚守良知捍卫真理。可以扫地扫厕所,但决不能放弃学术尊严。他宁愿一生受辱,也要将真知和真相告诉世人。他为真理而大无畏战斗的光辉一生,为20世纪知识分子矗立起一座丰碑。
作为黄万里教授长女,知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长孙女,黄且圆先生代表家属在座谈会上致词,娓娓道来黄万里先生在子女看来,是怎样的一位“普普通通的父亲”,为什么会感动那么多的人。
馆主曾受黄且圆先生之邀,出席了座谈会。会后她将讲话手稿交由馆主保存整理。未料数月后,2012年3月,黄先生因病不治逝世。馆主蒙杨乐院士信任,授权编辑黄先生遗著,2013年在科学出版社出版《大学者》一书。今日刊发此文,标题由馆主所拟,黄先生的讲稿内容略有修改。

著名水利学家黄万里教授在清华大学寓所书房
黄且圆:纪念父亲黄万里先生
父亲黄万里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今年是他诞辰的一百周年。对于子女来说,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父亲,我对他的记忆就像粼粼的波光,只是一段段、一片片地在那里闪耀,倒是别人的回忆、讨论、评价不时地激励着我,把记忆中的片断一点点地连接起来……
三岁左右时,一次父亲拉着我的手在散步,月光洒在一片光秃秃的土地上,那是父亲在四川三台工作的水利工地,我们家就在工地的边上。父亲边走边对我说:“我刚修好了一座桥,这座桥就用我的名字,叫万里桥。”那时父亲还很年轻,对自己的工作成绩兴奋不已。但事后我听说,祖父对此很不以为然,他批评父亲骄傲了,建议此桥从当地地名,命名为高家桥,并给刚出生的妹妹起名“无满”,以示警戒。就在这个工地上,一次日机来轰炸,一颗炸弹落在我家隔壁的院子里。上天保佑,那颗炸弹没爆炸,当大人们惊魂稍定时,看见我从床底下爬了出来。
三台的工程结束后,我家又搬回成都。父亲仍经常出差,勘查长江上游诸河流。一次看见父亲乘吉普回来,他满脸都是紫红色的小斑点,那是因流血结成的小伤疤。父亲告诉我们,路遇土匪劫车,开枪射击他乘坐的小车,子弹打在前窗的玻璃上,碎裂的玻璃又刺进他的脸部……这太危险了,万一子弹射中父亲的身体,那又该怎么办!还有一次,母亲带着两个不到四五岁的弟弟,去看望在野外勘测的父亲。回来途径绵阳,那边正发大水,许多灾民堵在河边准备抢渡,母亲好不容易登上最后一班渡轮,算逃过了一劫,而父亲还得坚守岗位。在当时险恶的工作条件下,他仍不忘写文章,像《金沙江道上》等,报道沿河的风土人情,特别是少数民族的生存状态,见诸报端。
抗战胜利后,全家回到南京,父亲应聘在水利部工作,这本是一个“美差”。但不久,水利部派遣他去江西任职。这里地处江南,河流湖泊遍布,是可以大施拳脚的机会,也还算是个美差,父亲甚至已到江西察访,准备履新。可是不久部里认为更需要人考察黄河中上游水情,解决甘肃省的干旱问题,于是又改派父亲到兰州任甘肃省水利局长兼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父亲二话没说,就带着全家奔赴兰州。
当时的兰州还很落后,市民的食用水是用牲口架着的木制水车,把黄河水拉往各家,倒入缸中。人们再在缸中加上明矾,等到沙石和赃物沉到缸底,河水变清后方能饮用。就是在市内,也能看到一些小孩子,因为没钱买裤子而光着下身。除了看家犬外,还有许多野狗满街乱窜。那时我只有八九岁,一次,天朦朦亮起身赶早上学,被狗咬了一口,还打过一阵子狂犬病预防针。可是父亲对这一切都毫不在意,他没有忘记改学水利,服务农民的初衷。他甫一到任就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他为该省水利工作拟定的方针是:先改善旧渠,次动新工;勘测全河西走廊的水资源以拟定通盘建设计划,很实在,绝不搞形象工程。
为勘察地质水文,他曾四下河西走廊向西到达玉门、安西、敦煌,甚至沙漠边缘的不毛之地民勤、红柳园等地。现在去这些地方并不困难,但在六十多年前,他得和同事们一起,坐骡车、骑马,甚至经常遇到劫匪。当时,新西兰共产党人路易·艾黎正在甘肃山丹办培黎学校,这是一所职业学校,半工半读不收学费,一方面吸收贫困家庭的孩子入学,也接纳处于困难境地的共产党干部的子女。父亲数次去山丹,帮助当地开发地下水,同时向为该校师生筹粮,为学生讲演。
父亲所到之处总是充满生气。他非常注意培养人才,特别是年轻人。在局里,他通常都是亲自授课,编讲义,外加对学员的考核。有一次,他从上海招来一批中专毕业生,对他们最初的培训就是学骑马。看到这一切,我们这些孩子兴奋极了,围着那几匹马又蹦又跳。这些年轻人后来很多都成了工程师,甚至是高级工程师。改革开放后,他们中还有人来看望过父亲。局里的京剧票友们自己排演了京剧《苏三起解》,演出时十分热闹。
记得刚到兰州没两天,一大早,父亲就带着全家去吃羊肉泡馍。他告诉我们,这是兰州最好吃的东西。饭馆的铺面只是一大间屋子,泥土地上放着方桌和窄条凳。端上的食物只是大块大块的肥羊肉煮成的汤,所谓的馍就是死面烙成的饼子。周围的人看起来都是干体力活的;这种东西最当饱,适合干重活的人吃,父亲就是这样说的。父亲大口大口地吃得很香,可是我只能勉强喝进几口汤,吃了一小块面饼。羊肉泡馍的确很当饱,我一整天都没再吃下其他东西。
每逢节假日,父亲常带我们外出游玩。到了黄河边,全家分乘两面羊皮筏子,羊皮筏子也就是在一个长方形的木排下,绑上几只全羊皮(去除了羊毛)吹成的气袋而已。羊皮筏子上既无扶手,亦无栏杆,汹涌浑浊的黄河水就在你的身旁,我们随着波浪一上一下地浮动、颠簸,可也有惊无险。
在父母的呵护下,兰州成了我童年最美好的回忆之一。即使到现在,每当我见到黄河,见到黄河母亲的塑像,见到那满是沟壑的黄色高原和脸上刻着同样深壑的高原老人的形象,心中都充满无限的感动,眼泪甚至会夺眶而出。

1948年黄万里先生在甘肃给水利工程师们讲课
1949年初,父亲感觉受到国民党特务的威胁,先把我们送往上海(他料到上海会比西北先被解放),自己出走香港。解放后他又乘香港至上海的第一班邮轮回到上海。其实,父亲是非常眷恋自己的故乡的。他在羁留北方后写过一首诗《清华园风雨忆江南》,其中有句子曰:“ 苦忆江南欲住难,羁栖北国少娱玩。少时力学图晚成,映水文心盼璀璨。镜里莫悲添白发,书成那得知音唤。案头埋首甘为牛,恐负江山扶枕叹。”江山虽美,可不得辜负她啊!
父亲在上海稍事逗留后,便应东北人民政府之聘,携全家到沈阳的东北水利局任职。从上世纪50年代起,他先回母校唐山交大(现西南交大),后经院系调整又到清华大学任教,开始了他50多年的教授生涯。他的思想活跃,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在交大实行了开卷考试。到清华后,他深感自己和工科出身的教师,需要在基础理论方面提高,特请了中科院的专家到水文教研室开概率、数理统计课。
到大学后他出差少了,但埋头苦干的工作作风不变。他著书、写论文,每天工作到深夜。即使到了文化大革命,父母三代同堂的家被塞进一间简易的学生宿舍里。那时大家受到压力,都不敢读书,搞业务了。父亲用书架把一间房子一分为二,一半是他和母亲的卧室,靠窗的一面放着他的书桌。除了到系里打扫卫生,做一些体力劳动之外,他都雷打不动地坐在自己的书桌前。
文革后期,父亲可在监督下进入当时的“三线”潼关以上地区,考察黄河、渭河的地貌和河势,同时在清华水利系驻三门峡的教学科研基地劳动和接受批判。此时,用他的话说是白天俯首听批,夜晚竭思治黄,对研究工作丝毫不肯放松。正因为他几十年一贯的努力,才能拟定出改建三门峡水库的方案,全面治理黄河的方案等等。更令我惊奇的是,他在被迫告别讲台的20多年后,还能给青年教师开出结合水利、水文应用的概率统计课。
父亲只知道坚持科学的真理,不论这真理多么令人难堪。当别人说“圣人出而黄河清”时,他却说黄河不可能变清,也无必要变清。当别人说在长江三峡上建坝是孙中山先生的宿愿,曾得到美国人的支持,其发电量可以照亮半个中国等等时,他却屡屡上书中央,高呼三峡高坝永不可修。
他只会说真话,不会说假话。对于学术观点是如此,对待政治问题也如此。自从戴上右冠之后,他受尽凌辱,但仍心胸坦然。一次他走在清华园里,被一名貌似工友的路人拦住,指着鼻子批判了整整一个小时。回到家中他仅仅对我们说:“如果他说的都是真话,他这样做也是对的。”
我们在家受到的最早的教育就是诚实,不可说谎。这个教育实施起来很简单:孩子犯了错误,只要自己承认,说出了真情,就不会受到惩罚,否则定是一顿痛打。有时我并没说谎,但父母不放心,竟让我白白挨一顿揍。时光荏苒,到我们成年后,位置倒转,我们也可以“训诫”父亲了。
文革后期,母亲就常常让我帮助父亲写检查。那时他对批林批孔运动想不通,便在家中说:“你们大伯是搞哲学的,可我对哲学一窍不通,但是孔子的哲学浅显易懂,我从小就接受了。”他更透露给我们:“我见过孔德成(孔子的后裔,1949年后去台湾),你们的外祖父还当过他的老师呢。”我立即告诉他,在会上不可这样说,会引来大祸的,他的回答却是:“我在会上已经交代过啦。”果然,为此他又遭到一次特大的批判。总之,在写检查方面,他从没有接受过我的“帮助”,一如既往地实话实说。父亲至死都是那样天真,像是《皇帝的新衣》中道出皇帝没穿衣服的孩子;而我们年轻的一代,却变得越来越老成、持重和犬儒。这种可悲的逆转,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1950年代黄万里先生在清华寓所备课
关于我国的水资源利用,父亲屡屡致信中央领导人,从毛泽东时代起直到他自己去世。他指出,三峡高坝不可修,主要因为自然地理环境中河床演变的问题,一个大坝建在河中,可以反过来影响河床、河流的水势,河流及两岸的地貌和生态等等。高坝的建成,会给国计民生带来极为不利,甚至是不可挽回的影响。他说黄河是一条利河,水少沙多,历史上南北漫流,形成了25万平方公里的黄淮海平原,是全世界最大的由河流淤积而成的三角洲,汉满蒙回各族人民在这里征战、融合,形成了伟大的中华民族,它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他甚至愤慨地声言:”说黄河是一条害河,是中国水利界的耻辱。”他认为中国的水资源丰富,所缺的是水量丰富地区的耕地,因此,以淹地换取电力是不可取的……
父亲的看法常与我国水利界主流的意见相左。撇开具体的技术问题和一些人为的因素不谈,这两种意见的出发点和背景就不相同。在父亲看来,人类赖以生存的河流和土地都是大自然的赐予。是大自然,包括阳光、土地、大海、山脉、河流等等,孕育出了人类。所以人类必须适应自然才能生存,人类也必须按照自然规律行事,与自然和谐相处,才能求得自身的发展。近些年来,自然灾害的频频发生,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日本地震引发的核污染等等,无一不向人们敲响警钟,将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再一次摆到我们的面前。我想,这才是父亲的观点越来越引起人们关注的根本原因。
去年(2010年,馆主注),一个令我们惊喜的消息传来:抗战时期父亲负责修建的涪江航道工程的一部分高家桥历经70年的天灾、人祸都没有倒塌,仍然屹立在那里,成为三台古堰永和堰的标志性工程之一。关于这座桥,中新社四川网记者兰婧在2009年12月22日的报道中这样说:
“怀着对这古堰的好奇,记者日前来到了永和堰的标志性的工程之一高家桥段。这是地处争胜乡坝南通向新德的一个石拱渡桥。桥体用花岗岩条石砌筑,高50多米,长约150米,宽4米余。由于两岸是滑坡台地,据说施工时用了三万多根青杠树棒(一种很坚实的树木,在水中永不腐烂,常作建材),逐台梯次打桩,编栏护坡。桥中间是渡槽,只两边不足一米宽处可通行人。远远看去,就像两条白色的缎带,搭连在青山绿树之间。走在桥上瞥见石拱下深深的水道,又不免让人心有余悸,只感叹这座出自著名水利专家黄万里先生之手的杰作,感叹当年工程之精妙雄伟、设计者之独具匠心。
黄万里先生是黄炎培之子,在美国主攻水利工程学,1937年回国后受三台县长郑献徵邀请,设计这座难度极大的渡槽,修成后取名‘万里桥’。黄炎培先生认为不妥,改以地名‘高家桥’,但当地老人仍称它为‘万里桥’。为此黄万里曾赋诗一首以纪念:‘我尝治水涪关道,三载移家到梓州。凿石开河资灌溉,一桥飞若彩虹浮。’”

1981年4月黄万里先生给清华水利系教师和研究生上课
父亲身前曾对我说过,他是公费出国留学的,花的是老百姓的钱,这座桥建在抗战最困难的时期,为了节约资金,因陋就简,使用的是最便宜的建材,先用一段时期,抗战胜利后还可重建。他还高兴地说,节约的钱就算偿还了留学的费用。他所谓的便宜建材大概就是指那种青扛树棒了。
70年后的今天,我第一次从照片上看到了万里桥。它朴实无华,谈不上雄伟,更没有“世界第一”;它的桥拱,就像父亲辛劳一生的脊背,驮着水渠,70年了,它把泊泊江水送往耕田,默默地滋养着这方土地上的农民繁养生息。
万里桥仍然屹立在那里,父亲在天之灵可以安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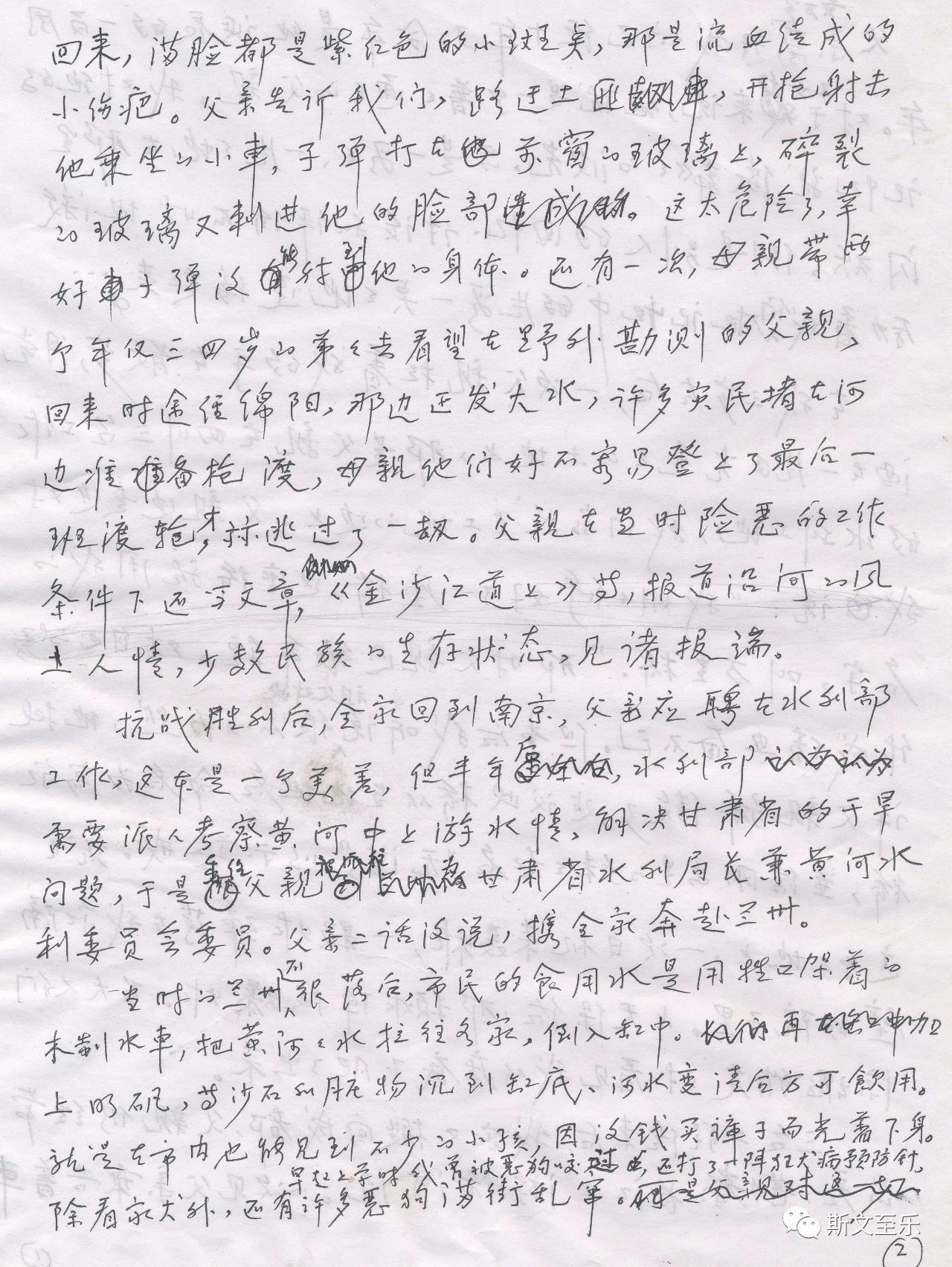
黄且圆先生本文手稿(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