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朝宗(1912-1998),福建福州人。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国语文学系。英国剑桥大学英国文学系研究生,回国担任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专于中西文学研究。曾任福建文联副主任、厦门文联主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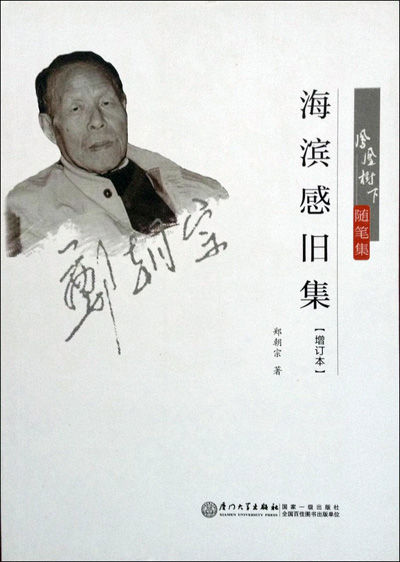
本文选自郑朝宗《海滨感旧集》(增订本),厦门大学出版社2014年5月版
铭清逝世,倏逾百日,清明节近,哀思弥切。念其生平为人,温良恭俭,居安思危,临变不惊,善处逆境,有足以淑世迪人者,作《怀清录》。
她悄悄地来到这世上,又悄悄地离去了,恰似生长在幽谷里的一朵小花,自开自落,不求人知。然而,她也并非无所作为,在一个小小的环境里,一个不显眼的岗位上,她聪明勇敢而又兢兢业业地做完了命运女神分配给她的一份麻烦琐碎的工作,70年间,未有差错。她禀性柔和,不骄不躁,看来虚弱,但当狂风吹到幽谷里来的时候,小花忽然变成青松,能顶住雪霜冰雹而毫不畏惧,她有一股平时不肯轻易外露的刚气。世间有曾经叱咤风云而后来陷入颓唐的巾帼英雄,也有能建功立业而却不善于持家教子的女中豪杰,和这些光辉照眼的人物相比,她自然显得碌碌无奇,她的名字是上不了史册的。然而,没有千千万万像她这样脚踏实地自强不息的平凡人作为后盾,少数杰出人物的丰功伟业怕也难以实现。也许是有鉴于此,当她逝世的消息传出时,凡是认识她的人都表示由衷的哀悼。“不愧清纯私谥定,岂关闻达举乡哀。”这副现成的挽联是可以移用在她身上的。
1916年3月,她出生于福州一个中级职员的家庭里。13岁那年母亲死在分娩中,遗下两个小弟弟,小的实际只有4岁。不久,父亲续了弦,又再生男育女,她自告奋勇把抚养同母弟的职责放在自己身上,对他们关心爱护,无微不至。她年纪虽小,却有志气,不慕荣华,一次到亲戚家里参加喜庆,偶然遭了冷遇,便抱着小弟回家,从此不再出去应酬。她的命真苦,19岁上父亲又因病逝世,家道中落,她的担子更重了。她自幼只在私塾里读书,和我订婚后,才要求到一家教会办的女中求学,那时她18岁。父亲死后,她要兼管家务,每天黎明即起,生火做饭,总是在微弱的灯光下边做家务边复习功课。午后放学归来,还要帮着洗晒一家的衣服,晚上也总是在微弱的灯光下读书到深夜。1936年夏天,我大学毕业,她已21岁了。我们是姨表兄妹,我父母看她孤苦伶仃怪可怜的,建议我们立即成婚。我没有反对,但有人散布流言说我有悔婚之意,这话传到她的耳朵里,她异常镇静,只要求和我见面一次问个究竟。原来她已决定,如果我真的负约,她不委曲求全,而要继承她父亲的职业去投考邮务局。云消雾散之后,她带着一颗真诚纯朴的心来到我家,以后不管发生什么情况,这颗心始终是坚如磐石的。

新婚燕尔——郑朝宗先生与夫人林铭清女士
我婚后一星期便出外谋生,两三个月中从汕头、上海流浪到北平,最后才在那里找到了职业。她在家里侍奉我的父母,我父亲向来喜欢她举止娴雅,得空便教她读古文;母亲欣赏她的针线活,常叫她给家里人缝制衣裳。这年12月我有了住处,写信回家建议把她接到北平,父母同意了。她北来后的第一心愿是,趁着眼前身边没有拖累,抓紧时间补课,以便暑假后继续去读完中学。我帮她补习英文,其余课程她有自学能力,特别是数学。她是不愿当一辈子的家庭妇女的,这我知道,可她的运气真坏,1937年暑假里卢沟桥一声炮响把她的希望彻底破灭了!7月下旬,北平的局势愈来愈紧,我们考虑要不要回南方去。一个星期天,我们到清华园去看望几位老同学,他们都走了。归途中参观了三贝子花园(即现在的北京西郊动物园),整个园子,除工作人员外,只有我们夫妇和两三个游客。她立即下决心说:“明天就走!”翌日午后,我们登上南下的火车,经过丰台和天津时,眼见日本军人荷枪实弹,在站台和天桥上,横冲直撞,盘查旅客,沿途车站上行李堆积如山。我们走后两天,从北平到浦口的火车停开了,倘不是她下的决心,我们就将流落在古城里,人生地不熟,老舍小说《四世同堂》描写的那些灾难很有可能落在我们头上,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不寒而栗啊!
抗日战争开始后头几年,我们的生活很不安定。为了另谋职业,我曾几度奔走于闽沪之间,把她安顿在上海哥哥家里。那时我的父母已迁往上海,她和从前一样在家侍奉两位老人。1939年秋天,哥哥介绍我到上海一家英国人办的学校当教师,从此我们才有了自己的家,我们在一起生活了四年。上海已成孤岛,租界以外全是敌伪的天下,真是寸步难行。我们住在亭子间里,她开始生男育女。那男的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那年生的,上海实行灯火管制,在一个严寒的夜里,婴儿出世,不小心着了凉,第3天起患了气管炎,全靠她细心调治,竟获平安。那女的也才2岁,几个月后染得百日咳症,又传给弟弟,在不短的期间里,小小的亭子间充满了令人听了心裂的奇怪的幼儿咳嗽声。我真佩服她的耐心和勇气,在困难面前不低头,终于安全地渡过难关。那几年我自己也常生病。有一次得了副伤寒,连续7天,总是夜里发高烧,早上热退照常到学校上课。后来自觉不妙,才由哥哥和她陪着到一家教会医院求诊,医生检查了我的胸部,悄悄地告诉他们病情险恶,能否脱险要看夜里情况如何。那时的医院是不准家属陪伴病人的,我住进了病房,她来告别,态度和平时一样镇静,只嘱咐几句就走了。其实她心里非常难过,只是善于克制。那天夜里我做了许多噩梦,天快亮时出了一身冷汗,觉得舒服多了。早上医生来察看,说病已好转。一星期后,我出院了。1942年12月,日本人接收了英国人办的那个学校,我想方设法辞去教职,于翌年7月重返福建。那是大热天,我乘船到宁波,从那里步行21天回福州,一路虽辛苦,却是单身出门,没有拖累。一个月后,她带着两个幼儿搭帆船,从浙江沈家门沿着海岸线漂回福州,途中浪涌涛翻,惊险万状,别的旅客叫喊哭泣,而她一心都在孩子身上,抱持救护,唯恐不及,一点不惊慌,更不知什么叫辛苦。这是和她结伴同行的一位亲戚告诉我的。
抗战末期,我终于在厦门大学扎了根,不再到处流浪了。那一时期以及接着来的三年解放战争时期,是我们一生所经历的第一个困难时期,每月收入总赶不上飞涨的物价,她又生下了两个女儿,一家六口的生计全凭这巧妇去安排,才得勉强度日。1949年及此后几年,她很兴奋,常去参加校内教职工眷属组织的活动,有人劝她出来就业,她很愿意,估量自己当个会计还是可以的。但她权衡利害,认为出外做事,不如留在家管好儿女。她是世间第一等的慈母,从心坎里疼爱她的4个孩子,每逢孩子生病发高烧,她总是心急如焚,彻夜不眠,每隔十几分钟便给他(她)量体温,灌开水,完全不知疲倦。但她对孩子的管教却是严格的,决不允许他们有一点点的坏习气,孩子有了过错,她不滥施体罚,只抓住不放,每次总要谆谆训诲—两天。这办法果然有效,4个孩子,从幼小到成人,从没在外边做过—件违反规章的事,也从没受过任何方式的处分。他们和她—样一直是谦虚谨慎的。遗憾的是,她管得住孩子,却改变不了我鲁莽急躁的脾气。那几年天下虽然太平,阶级斗争的弦却拉得很紧,对此她感到忧虑,时时劝告我要平心静气,少发议论。我没听她的话,果然在一次“运动”中,一个跟头栽到“泥潭”中去了。后来虽然归了队,但在整整20年中成了不可接触的“黑人”。我是咎由自取,而她却无辜受累。真金不怕烈火,她是经得起考验的,无论处顺境或逆境,始终保持本色,从前既不自矜,现在也不自馁,态度总是那么安详。特别是在那戾气冲天的10年,许多人惊慌失措,而她常用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颜色面对来犯的人。她不怕死,抗战期间,在长汀和福州,日本飞机无法把她赶进防空洞,当别人都疏散到城外去时,她独个儿在家里看守门户。她也不怕困难,无论手边如何拮据,决不随便向人借贷,也决不让孩子们中断学业,有一时期她用双手支持他们继续上学。她疼爱孩子,但在利害关头上又舍得让他们去冒不得不冒的危险。“文革”初期号召青年“步行串连”,两个小的女孩都只有20岁上下,她明知此去凶多吉少,却硬着心肠让她们报名参加。她们参加的是一支远征到重庆的队伍,出发时经过里弄门口,她去看望,回到家里脸有泪痕,我知道她心里是痛苦的,然而她并不懊悔。几个月后,她们平安回来了,大的接受毕业分配,小的奉命上山下乡,她又叫她立即去报名参加。后来的事实证明她这样做是很有远见的,她真是理智的化身!1970年夏天,我下放连城县,事前组织上派人通知她不必下去,她坚持要去。在乡下两年,她学会养鸡种菜,和农民相处很好,他们都称她作“老林”。她从来不怕生活艰苦,她要的是精神上的愉快。
雨过天晴,十年浩劫消于一旦,随着国运的好转,我家也回归顺境。孩子们都各自成家立业去了,家里冷清清的剩下我们两个老人。有人劝她珍惜余年,享点清福,她还是我行我素,无动于衷。她一生不知清闲为何物,儿女的事忙完了,还有孙子的事,她的两手不会插在腰上或塞进袖子里去的。这一时期,她唯一不同于以往的表现是夜里能熟睡,多年的失眠症忽然消失,一向消瘦的容颜也逐渐丰满起来,我们一家都为她高兴。然而,我却得了老年性的疾病,无法根治,而又旷日持久,难为她年逾花甲还要长期充当我的“家庭护士”。彼此都已到了暮年,心里明白自然规律不可违抗,早晚是要分手的,我自揣必先她而去,谁知造化弄人竟至如此,我还在苟延残喘,而她却一病不起!她生平难得生病,即使病了发烧,也总要挣扎起床,照常料理家务。我们都以为她体质好,耐力强,哪知一颗“定时炸弹”早已隐伏在她的肠胃里。她有呕吐的习惯,几十年来,常在吃饭的时候,忽感恶心,到了冬天,则非吐不可,喝了杯开水,也就过去了。她说这是胃冷引起的,不碍事。我们劝她找个医生诊治,她总不听。这次发病前两个月,她陪我出差,由于旅途辛苦,回来后一直感觉疲劳,常见她坐在藤椅上边织毛衣边发呆,似乎有什么心事,劝她到医院去检查,她又一推再推。那一时期,每天晚上她总要拉我出去散步。晚饭后,我们从西村出发,经过学校西门便进入校园,慢步登上小丘,在大礼堂前伫立望着大海,听涛声;然后下山折入芙蓉园,那是个美丽的地方,教学楼、本科学生宿舍、研究生宿舍都在周围,山上山下一片灯光,有一口人工湖,湖边刚摆好石椅,天冷了,坐着不方便,我们期待明年夏天来此乘凉;出了芙蓉园,沿着北去的大路绕到南普陀,逗留片刻,再从那里回到西村:这是我们固定的路线。11月1日晚上,我们仍旧出去散步,7时归来,她还是好好儿的。9时半她到厨房刷牙,忽感胃痛,呕吐一阵,喝了些开水,上床后呻吟大作,一切老办法(喝水、擦万金油)全都失效。折磨到11时,我看情形不妙,急忙挣扎到北村宿舍找二女儿和女婿,他们疑心是急性胃肠炎,用自行车扶送到学校医院。翌日校医诊断为急性胰腺炎,急转市立第一医院,从此她不再回来了!
她住院50天,病情自始至终都是险恶的,中间出现反复多变的情况。她的态度坚忍冷静,一如常日,不论对她采取什么样的疗法,她都愿意接受,直到血管僵硬连针都扎不进去了,她还是默默无声地忍受着,医师称赞她是个最善于配合的病人。她谦恭成性,住院后许多亲友来看她,系里还安排女教师和女同学来参加护理,她深感不安,吩咐我们婉言谢绝。后来在外地工作的两个孩子回来了,连同身边的两个,一共4人日夜轮流护理,她才安下心来。她为儿女辛苦四十多年,而她们才为她尽孝四十多天,对这样微薄的报答,她心满意足。她入院后几天,我也住进第一医院的高干病房,我家六口又团聚了,虽然是含着眼泪的团聚,她却以为这是最大的安慰和幸福。她自知重病难医,又觉得已尽了人生应尽的责任,可以安心休息了,她不畏死。但她在病中偶尔也露出一点求生的欲望,她的病床是靠窗的,一天午后我去看她,她正戴着眼镜仰望对面山上的护士楼,灿烂的阳光照着楼墙,她忽然发出微弱的声音说:“什么时候我们再能一起到山上去散步啊!”我听了心里一震,直觉肝肠寸断。无可奈何的一天终于到来了,那是冬至日,早上我进入病房,两个女儿正在替她梳头、洗脸、擦身、更衣,这是每天例行的工作。她有洁癖,平时指甲、趾甲都要修得短短的,不让有一点污垢,病中也还是如此。“质本洁来还洁去”,她要带着干净的一身离开人间。9时左右,我正跟她说着话,只见她双眼一翻,忽然进入休克状态。当内科主任赶来抢救时,她睁开眼睛,点头致谢。她生不累人,死也不拖延时刻,弥留的时间很短,晚上7时46分,她停止了呼吸。在她患病期间,天气一直是晴好的,她的遗体送到火葬场去的那天下午,一片明丽的阳光笼罩着海市。
这就是一个平凡人的一生,不会载入史册,更不会成为小说的题材。然而,我相信平凡之中有伟大,她的整个人格说明了这一点。她虽没有给国家民族立过功,也没有做出什么特殊的贡献,可是国家民族要生存和发展却无论如何不能缺少无数像她这样的公民。从这意义上看,她以及与她相类似的中国普通妇女真不愧称为鲁迅所说的“中国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