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闻恩师溘然长逝,难抑心中悲恸。先生的离世,不仅是科学界的巨大损失,更让我失去了一位毕生追随的导师与精神楷模。提笔之际,先生报国之热忱、治学之严谨、为人之谦和犹在眼前。在此,为悼念我的先生,讲讲我和他的故事。

2023年李德平院士在钱三强先生诞辰110周年之际接受采访
1989年夏天,初入核工业系统的我,因为一个偶然机会和一次特殊任务,结识我的导师——李德平先生。在短短的两周任务期间,他扎实的数理知识、敏捷的逻辑思维、娓娓道来的扣问,让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第一次窥见了学术的真容,也在我年轻的心里播下了一颗想追随先生的种子。
1996年,我有幸成为了先生的正式入门弟子,开启了博士研究生的求学之路。九月入学后,当我第一次以学生身份拜见先生时,他讲道:“学生是学出来,不是老师讲出来的,学生必须读书、必须研读本学科所有重要历史文献和最新文献,以时代的视角和眼光看本学科方向的过去、当前和未来。”同时,他要求我们同届同学坚持每周交流文献学习心得,限时5分钟,把自己阅读文献的最大收获传递给大家,通过“一人读文献,大家共同读文献”,做到加倍扩展知识面。我们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坚持了一个学期后,都感叹说:“李先生这招高,真高!”
第一学年后,其他同学纷纷进入博士生论文开题方向的文献阅读。先生对我要求:“从现在开始,你必须从国际放射防护委员会(ICRP)第1号出版物读起,一直读到现在最新的出版物,即ICRP第60号出版物,每周必须交一份所读这些出版物的读书心得。”我还记得研读ICRP第26号出版物时,读了三周才过关。
同时,他建议我开始核设施严重事故情况下航空应急测量技术方面的文献调研和学习,为论文开题做准备。当时他对我讲:“我的职责就是把你带到一个学术方向的前沿,其余就是你的事了。”看了我几秒后,他又严肃补充说:“你不找我,我也不会找你。不说清楚不开题、没有想法不开题、不知道做点别人未做的事不开题。”
就这样两年过去了,有一天他把我叫到他家,对我语重心长说:“森林,三个月后正式做开题报告,论文题目就是严重事故情况下航空应急监测技术研究,重点是严重事故情况下人工放射性核素航空应急监测的定值问题。”
先生指出,当时的我在理论计算方面还可以,但是测量技术底子太薄,让我找中辐院任晓娜、原子能院陈凌,一起先做些航空NaI晶体性能方面的实验测量。
这次见面快结束时,先生说导师指导组除他自己外,还有张永兴(原子能院)、胡遵素(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顾仁康(核工业航测遥感中心)。“好一个庞大的、高规格的导师组!”当时一听,我真是有点头大、直冒汗。就这样,我开始了博士论文开题准备工作。
开题报告的第一关,是蒙特卡罗(MC)模拟计算。先生首先问我:“研究生院有哪些老师开MC课?”在我答有四位老师后,他说:“你必须去听裴鹿成老师的课。”
一学期下来,我MC课程考试成绩还不错,但先生仅仅说“基本过关”,进而要求我对航空NaI探测器及其结构、固定翼飞机、地面点源、地面面源、空中烟羽分布源进行MC模拟。
待3月后初步模拟基本过关,先生继续要求我针对飞机飞行高度、飞行速度、飞行航迹、空中氡浓度等进行模拟。就这样,仅是一个MC模拟,一个学期就这样过去了。1998年2月底,我的博士论文正式开题,5月开始我在核工业航测遥感中心开展各种基础实验。
接下来是论文实验工作的第二关。1998年10月开始飞行试验,实验结果与理论模拟结果相差17%。先生说不行,必须找原因。由于课题经费有限,再次飞行试验只有等待核工业航测遥感中心有飞行任务时才能安排。就这样断断续续一直到1999年3月,我都没有找出相差原因在哪里。同期同学在8月安排答辩,我却遥遥无期。直到2002年5月,又一次实地飞行结果表明差异在10%内,也找到了有实际证据的原因,先生这才说,“先可以考虑毕业吧”。我因此深深地体会到老先生的治学严谨。
之后我迎来论文答辩的第三关。在论文最终定稿一个月前,先生叫我到家里,说论文还可以修改。我一听“全身炸毛”。我的论文工作有一部分是涉及固定翼飞机穿越烟羽,用飞行穿越实验测量数据,快速刻画事故排放烟羽轮廓或姿态,及其传输走向趋势。当时问题并不是实验结果与理论分析的差异,而是他发现我的理论推导可以有更好的方法。
我听完后心里有些情绪,因为当年答辩时间已非常临近,既面临无法答辩也面临取消学籍的风险。但他很坚持,“论文必须修改”。我眼巴巴地望着他,他也直直地瞪着我。不知道过去了多长时间,他轻声对我说:“看看这篇最新文献和我的推导,你还可以超过他们。”
我说我拿回家看,他说:“就这里看。你不是说时间不够吗,就在这里看。”
再次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红着脸说:“我明白了。”
“你明白什么了?说说看。”
我一边说,一边写。
一个小时过后,“好吧,就这样”,他讲道。
这时,我们俩才难得地齐声笑起来了,这件事令我终生难忘。先生的倾囊传授、先生的高尚无私,令我永远敬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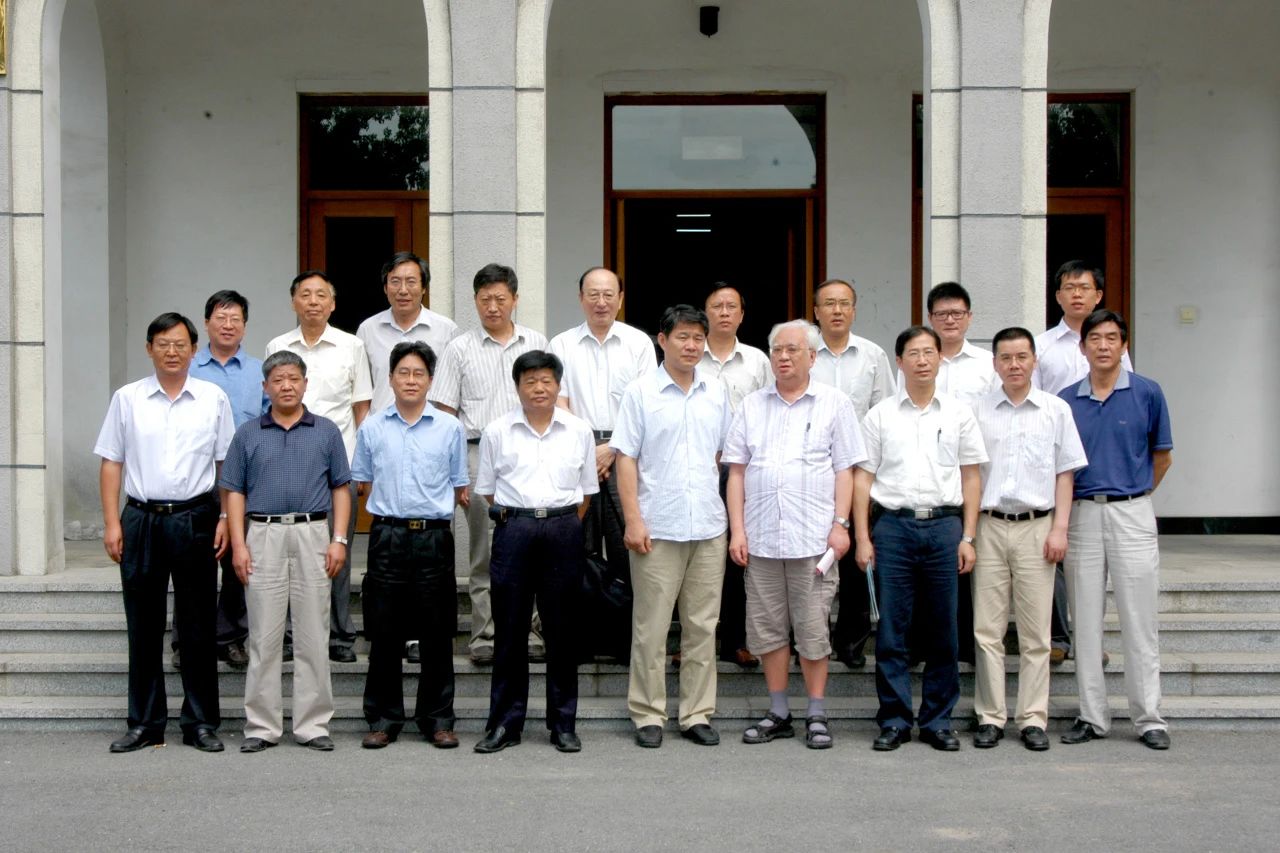
前排右4为李德平院士,前排左1为刘森林
1948年先生毕业之时,中国核工业尚处萌芽,辐射防护领域更是一片空白。先生怀揣“科学救国”之志,1950年进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原子能院前身),从此将一生献给了核科学与辐射防护事业。1984年,先生以卓越学识登上国际舞台,连任三届国际放射防护委员会(ICRP)主委会委员,担任联合国原子辐射效应科学委员会(UNSCEAR)中国代表,推动中国核安全理念走向世界。如今,我接替他担任这些职务,每逢奔走于国际组织间,总能想起先生的殷殷嘱托。
作为先生的学生,我亲历了他治学的严谨和对教育的倾注。先生一生以“较真”著称,他坚持辐射防护的核心在于“防止可避免的照射”,并强调“剂量限值并非安全分界线”,这些理念曾被视为“固执”,却成为行业准则。先生晚年仍坚持“知识分享”理念,其治学严谨、平易近人的风范令人敬重。
2006年,我有幸在北京为先生主持80岁寿宴,彼时他已退居二线,却仍坚持每日伏案工作。2018年,92岁的先生亲临原子能院辐射安全研究所(核安全与环境工程技术研究所前身)成立60周年纪念大会,在满堂掌声中为学科发展擘画新章。

辐射安全研究所成立60周年现场,李德平院士亲临现场并发言
先生常道:“世界上唯有知识给了别人而自己不会减少。”他就像一支闪闪发光的知识蜡烛,燃烧了自己,却点燃了他人的智慧之光。他渊博的科学知识、严谨的治学态度、高尚的大家风范深受我辈敬仰。
先生安息!您将永驻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