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吾土吾民:农民的文化表达与主体性》后记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沙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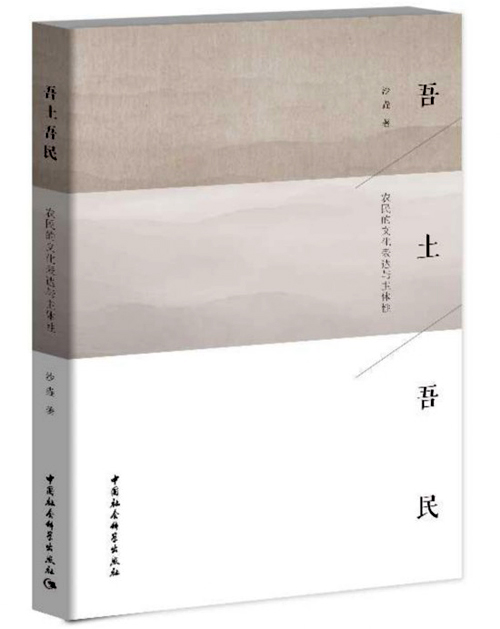
2006年9月,我在自己的日记本上写下一句话“这个夏天的记忆,属于黄土地上这群敲着碗碗、弹着月琴的皮影艺人。”
2006年8月初,怀着对十三朝古都的朝圣之心,我来到关中大地,第一次见到了皮影戏。皮影戏,如同那个从《大明宫词》里走出的女子,惊呆了将军的马匹,踢翻了我人生的花篮。
十年清华,九年皮影。
我把这九年,分成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2006年3月至2007年10月,这一期间,皮影戏在我心中是奄奄一息的“民间瑰宝”,是亟待抢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至今犹记得2005年前后,媒体上对非遗要不要保护,如何保护的讨论,一浪高过一浪,有几篇关于皮影戏的文章犹在耳际,对我影响深远。尤其是2004年4月皮影艺人姜建合做客《乡约》,播出了专题片《最后的华县皮影》,以及2005年2月《新京报》发表《最后的华县皮影》,记录了在2004年年底华县原生态的皮影演出以及皮影老艺人的故事。感谢赵海涛兄把视频和文章发给我,让我泪流满面,并直接促成我对皮影戏的研究。
我有幸见证并参与了这场关于非遗的大讨论。2006年3月,我通过在网络上发表散文、博客,在清华参加公共演讲比赛等方式呼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直至国家公布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以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一锤定音:非遗必须抢救。因为事关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和民族记忆,如冯骥才所说“如果文化消失了,民族也就没了。”①
这一阶段,我对皮影戏的认识是感性的。无论是看皮影的,还是演皮影的,都是没有几根头发或没有几颗牙齿的老人。他们守着千年古老的艺术,口头禅是“毕了……毕了……”,可是他们对艺术的热爱与执着深深地感动着我。
抢救皮影戏,这是2006年我灵魂深处的声音。因此,第一次来到华县农村,我带着强烈的要拯救他们的精英意识。或许,也可以说是初为知识分子的一种使命和责任。

2015年7月3日,清华大学校长邱勇在2015届毕业生沙垚的处女作《土门日记—华县皮影田野调查手记》上签名,作为毕业纪念。
但其实,我并没有做好太多的准备。我们只有一个简单的信念:只要全社会关注了、参与了,文化就不会消失。那么,如何让更多的人关注和参与呢?有三个较为常见的路径:
第一,政府从理念、政策到财政全方位的支持非遗传承与保护。
第二,借助大众媒介发声,用饱满的热情,呼吁公众对本民族文化的关心。
第三,利用摄影、摄像、录音等数字技术,保留民间艺术,为后代至少留下一些影音资料。
但是,然后呢?
不同的社会主体来传承和保护非遗,可能将非遗引入完全不同的道路。这些问题,在2005年前后,很少考虑。
2007年底,我迷上了人类学。
感谢清华大学“星火计划”,让我有机会再赴关中大地,聆听皮影戏。梁君健兄建议我把皮影戏的调查做成一个更深入、更持久的民族志。从此,学术之路漫漫,吾上下而求索。
这时候,华县出现了一家文化公司,给皮影艺人发工资,组织排练创新,录制抢救濒危剧目,打造民间文化品牌,走上世界舞台……可是它也垄断了所有皮影演出,农村看不到戏了。应该如何分析与看待这一现象?在非遗的框架之内,很难找到答案。
于是,我开始挑战非遗理论,提出一个反问:为什么要传承皮影戏?后来才知道这个简单的问题里面有着多重文化人类学的基本问题。比如,文化有没有固有的生老病死的生命特征,文化传承的意义是什么?该意义对于我和村民有何差异,等等。
但为了探寻这个简单问题的答案,我形成如下两个方面的转向与基本假设:
第一,我转向历史,并有一个基本假设,既然当代皮影戏衰败了,这说明它曾经繁荣过,分析当下衰败的原因,不如去看看当年它是如何繁荣以及为何繁荣,又是什么样的机缘让它转向衰败。
第二,我转向社会,也有一个基本假设,一个具体文化形态的衰败是由于它与社会结构互动的断裂。那么,就应当去看看它繁荣的时候,与社会为什么以及如何能够良好地、有机地互动。
从2007年底到2009年10月,这期间,我阅读了大量人类学的经典作品,我学会了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学会了倾听和记录,而不再是自诩精英,对农民艺人指手画脚告诉他们应该如何传承文化。当我第一次看到“民族志”这三个字的时候,兴奋不已。
2007年冬,我和几位同学“仗剑踏雪入潼关”,豪气干云。这份热情和理想、对未知世界充满好奇的精神,以及在关中大地上度过美好的青春岁月和无数的回忆,令我此生无法忘怀。
我对自己“局外人”与“文化他者”的研究身份进行了反思,意识到要了解皮影戏的兴衰存亡,必须学会从当地人的视角看待世界、理解问题。皮影艺人的言语、行为,甚至类似于“挤眼”的小动作,都是他们对世界认知和解释的方式,而我要做的是“观察、记录、分析”,把这些“转瞬即逝的时刻和事件”从“时间中解救出来”,即所谓的“深描”。②
我特别想知道,皮影艺人心中真实的皮影戏是什么样的,他们有什么样的感情,会如何讲述自己的故事。为此,我跟他们一起跋山涉水、浪迹江湖,喝过酒饿过肚子,坑过别人也被别人坑过……建立起深厚的情义。
从此,在我的脸上,也偶尔可以看到只有人类学者才有的坏笑。
这是我研究皮影戏的第二个阶段,逐渐形成了一些自己的学术思考。我把皮影戏看作关中农村一种喜闻乐见的本土化的传播媒介,从村民和皮影艺人的视角来理解影戏这种媒介在中国农村社会和乡村生活语境中的作用和变迁。因此,这一阶段,我试图讲述的皮影戏的故事,已经不是一部静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或艺术的发展史,而是一部活生生的由人物故事和历史场景所构成的社会文化史。皮影犹如一枝离弦之箭,其靶心则是和皮影相关的人的生活,以及这些生活所根植的社会文化与历史的变迁。
在无数怀疑的目光中,“你的研究是传播学吗?”一个传播学的学子带着皮影戏的故事,执着地回到了传播学。2011年,我决意攻读传播学博士学位。从此开始了我皮影戏研究的第三个阶段。
我必须要从传播学的理论汪洋中寻找脉络,支撑皮影戏研究的“合法性”。同时,我也开始思考,既然皮影戏是传播现象,为什么对皮影戏的研究却不是传播学研究?或许是这个学科发展本身遇到了某种对象化依赖的困境。
进入博士阶段之后,我结识了赵月枝教授。恰好近年来她将传播政治经济学转向乡村,认为在城市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媒体(现代)中心主义和发展主义等诸多范式的主导下,乡村出现文化困境,提倡将乡村文化传播的问题与社会整体运行、历史变迁、制度安排等联系起来考察,才可能有所突破。她与我在北大一个会议的间歇,“溜”到休息室,畅谈了近3个小时,她的思想如“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瞬间奠定了我博士论文的主基调。她不断追问,中国的农民有没有文化,中国农民的文化是什么?成为我博士论文的主要研究问题。
是她激活了我大量的田野资料和历史档案,我开始意识到皮影戏的兴衰,不仅关乎皮影本身,还关乎农村社会的变迁。蓦然回首,我发现自己曾经纠结的皮影戏是不是传播学范畴,是一个多么幼稚的问题。一幅20世纪中国乡村文化传播的历史画卷正在徐徐打开。
于是有了这本书。
--------------
① 孟兰英:《冯骥才:民间文化守望者》,《今日中国论坛》2006年第10期。
② 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韩莉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21-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