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翟中和(1930-)1930年8月生,江苏凓阳人,我国著名细胞生物学家。1950-1951年在清华大学学习,1951-1956年留学苏联,毕业于前苏联列宁格勒大学。1959 -1961年在前苏联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进修。1984-1986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生物学系做访问教授。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院士。现为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翟中和教授在我国较早建立细胞超微结构技术,首次研制成鸭瘟细胞疫苗,在动物病毒复制与细胞结构关系的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要进行核骨架—核纤层—中间纤维体系、非细胞体系核重建、细胞凋亡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许多创新成果,被国内外所引用。先后在国内外发表论文280余篇,专著15部。他主编的《细胞生物学》被评为全国高校优秀教材奖一等奖,是国内同类教材中影响最大的一部,已发行50余万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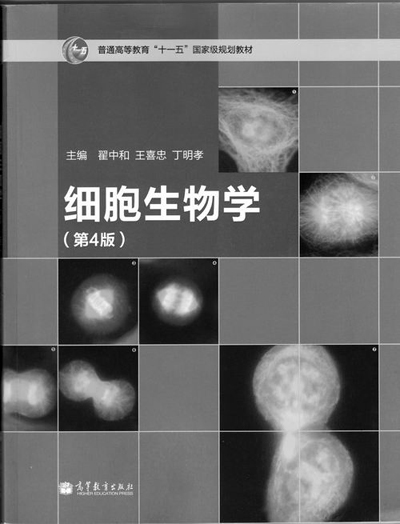
翟中和教授主持编写的《细胞生物学》教科书第四版
艰苦环境铸就良好素质
翟中和,1930年8月18日出生在江苏省溧阳与宜兴交界的一个农村水乡。8岁的时候,他的母亲因病去世,慈爱善良的祖母担起了抚养他的责任。翟中和7岁开始在当地的一所非常偏僻而简陋的乡间初级小学接受启蒙教育。一位严厉的先生讲授小学1-4年级所有的课程,每个年级先生只能讲15分钟,其余的时间就要靠自学。艰苦的环境,使他从小就养成了独立学习与独立思考的习惯,对他今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初小四年级,刚满10岁的翟中和,就要到离家六里远的一所完全小学去读书了。那时正值抗日战争,四处兵荒马乱,家中的情况日渐困窘。他早晨只能喝一点粥,很早就要出发去学校。初冬的江南水乡,稻田在湿冷的空气中微微透出光芒。天空阴霾而低沉,常常大雨伴着骤风,如注而下。10岁的翟中和光着脚丫,把油纸伞的伞柄顶在自己的肚子上,踩着泥泞的小路,逆风走向离家六里远的学校。
初中的三年,时局依然动荡不安,翟中和转了三次学才读完初中。1946年,他考入了江苏省立溧阳中学。高中时的翟中和除了对文学有兴趣,对其他学科并没有太明显的喜恶,各科成绩也比较均衡。他给自己的评价是:“缺乏抽象逻辑思维的能力,推导公式的能力差,数理类或工程类不是我能力所及的专业。”在考大学前,他仔细考量了自己的优势和特点,并结合所处的环境,作出了大学进入生物学系学习的重要决定。当时要填报高考志愿表时,翟中和开始填写了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他的同班同学无意中看到他的志愿表,便问他为何不报考清华大学?他想了想,觉得也可以,就涂掉了原来的志愿,重新填报为清华大学生物系。就这样,翟中和考入了清华大学。
翟中和的少年时代没有受到良好而系统的教育,但艰苦的条件锻炼了他自学自律的能力,培养了他承受巨大困难的心理素质和毅力。他一生中从不怨天尤人,从无怀才不遇之悲,在任何情况下他都充满希望,勇往直前。
1950年,翟中和从江苏农村来到北京,进入了清华大学,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活。清华园的一切都使他感到陌生和神秘。“我第一次看到了实验室和图书馆,第一次看到了显微镜,第一次使用自来水和电灯……”他在清华大学生物系的一年级就先后聆听了著名生物学家陈帧、赵以炳和沈同等教授开设的普通生物学课程,李继侗教授讲授的植物学以及张青莲教授讲授的普通化学。这些知名的老师把复杂的课程讲得深入浅出,引人入胜的内容把这位来自农村、穿着大褂的学生引入了一片崭新的天地。
1951年,翟中和通过了教育部选派苏联留学生的考试,作为新中国第一批公派留学生,被派往苏联学习。临行前,周总理在北京饭店宴请他们。翟中和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刘少奇讲过的话:“新中国刚建立,现在国家还很穷,打仗、打天下是我们老一辈的责任,你们的责任就是建设祖国,所以在苏联学习要尽量考5分。”
翟中和被派往苏联列宁格勒大学生物系学习,他分外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到了苏联一切都为了保证学业,其他的什么都不想。他的成绩单一目了然:除了一门历史唯物主义考了4分,其他的44门课程全部考了5分。要知道他到苏联的时候,是完全不懂俄语的!这个成绩的取得,必然是付出了巨大的努力。1957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到北大访问,翟中和给他当翻译,这位官员表扬他说:“你的口音很纯正!”
历经磨难,痴心不改
1956年,26岁的翟中和带着优秀毕业生的荣誉从列宁格勒大学毕业了。因为1952年院系调整,当时的清华大学生物系与北大动物学、植物学两系及燕京大学生物学系合并为新的北大生物学系。北大生物系系主任张景钺和副系主任张龙翔希望翟中和可以来北大工作,征求他的意见时,翟中和很老实地回答说:“这不由我决定,要服从组织分配,组织分配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就这样,翟中和被分配在了北京大学生物系任教,先后随同李汝祺教授和沈同教授做助教,从事遗传学和放射生物学的研究。

早年的翟中和先生
1959年,翟中和再次被派往苏联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进修,主攻电子显微镜技术和生物电子显微学,师从弗兰克院士和别里科夫斯卡娅通讯院士。别里科夫斯卡娅曾经是美国遗传学家穆勒的学生和助手,翟中和评价她“是一位真正的科学家”。当时她已年逾六十,但精力过人,对这位中国弟子言传身教,悉心指导,这些都对翟中和的学术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翟中和在后来的回忆中认为“这段时间是我科学研究工作的真正入门”。应用电子显微镜研究细胞超微结构在当时是很先进的技术,这一选择使翟中和受益匪浅,以后的数十年里他和他的学生、助手应用电子显微镜与其他技术相结合,在细胞生物学方面做了很多系统而有特色的工作,成为我国生物电子显微学的重要开拓者之一。
1961年,翟中和回到北京大学,次年任讲师。在当时的中国,科研条件极其简陋,加之政治运动不断,很多科学研究工作停滞不前,要做一点工作是很困难的。然而,翟中和最可贵的地方恰恰在于其在困难重重的条件下并没有放弃科学研究,反而以一种饱满向上的积极态度,因地制宜,在艰苦情况下创造条件,坚持做实验、做研究。
1969年,翟中和被下放到江西鲤鱼洲干校劳动锻炼。尽管感觉不公平,翟中和却仍然能够认真对待自己在干校里的“工作”——养猪和种水稻。他把猪养得又肥又壮;他作为班长的一个种稻班,水稻年年丰产,被称为“水稻丰产班”。因为表现突出,他被评选为江西省劳动先进分子,还曾到井冈山参加省里的先进分子表彰大会。
1973年,翟中和回到了北京。北京大学生物学系已经开始逐步恢复日常教学和科研工作,但工作条件和设备仍然很差。结合当时的特定条件,翟中和完全凭借对科研的热情和执着追求,历经十年的努力,在家禽、家畜治病病毒的分离、鉴定和疫苗研制方面做了很多有意义、有实践价值的工作,并“在畜牧兽医界小有名气”。在进行应用性科研工作的同时,翟中和对病毒细胞关系这一基础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利用电子显微镜等手段,对多种致病病毒在细胞内的复制、装配及其与细胞超微结构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研究,发表了六十余篇论文,组成一个有特色、有活力、有创造的科研集体,并为后来成立的细胞生物学专业打下了基础。
重学问,淡名利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真正迎来了“科学的春天”。而在此前的二十多年,随着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生物科学在国际上的发展异常迅猛。随着工作的不断深入,翟中和深感自己原来研究的超微结构形态学已经跟不上形势发展,需要在科研中引入分子生物学技术。基于这样的考虑,1985年至1986年,已经是教授和博士生导师的翟中和,在年届55岁时第三次远赴海外求知。这次他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生物学系佩曼(S.Penman)教授的实验室做访问教授,从事细胞核骨架及其与基因表达关系的研究。翟中和意识到我国的生命科学发展水平已经远远落后于国外,“只有不断调整方向与步伐才能跟上形势。选择先进的、有理论意义的又适合我们实际情况的科研课题成为我们继续前进的关键问题。”

前排右2为翟中和
在美国的学习时间只有短短的一年半,翟中和格外珍惜这个机会,恨不能延长每天24个小时,争分夺秒地工作。忘我的工作也让翟中和付出了健康的代价,长期的饮食失调,使他患上了糖尿病。翟中和只能暂时依靠一些药物缓解病情,同时坚持在实验室里工作,就这样一直坚持到回国。即使是在这样的身体状况下,翟中和在美国的一年半时间里仍然发表了3篇论文。“我并不聪明,我最大的优势就是勤奋。我相信勤能补拙。”这是翟中和认为自己能在专业领域取得成绩最重要的原因。
从美国回国以后,经过较长的分析与考虑,翟中和决定选择“细胞核骨架—核纤层中间纤维体系”的研究作为主攻方向之一。核骨架与核纤层是否存在当时有争议,然而这一问题的研究对解释细胞核与染色体的结构与功能会产生新的概念。历经翟中和与他的五、六届研究生十多年的艰苦奋战,这一领域的研究真正与世界接轨了,此后他们的研究工作步入系统性,发表五十多篇论文,其中多篇论文被国外重复引用。
1991年,翟中和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这之后,他除了科学研究,每天更多了很多事务性的工作。他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挂了一幅字,上书:“重学问,淡名利”六个大字,提醒自己以做学问为重中之重。这时的翟中和仍然坚持指导学生,包括在实验室做论文的本科生的工作,他都要过问,并亲自帮他们修改论文、听预答辩。
从1978年北京大学建立细胞生物学专业至今,在翟中和的带领下,从建立学科、开设细胞生物学课程,到建立博士点、成立细胞生物学研究所,再到现在建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将北大的细胞生物学从无到有,建设为现在中国高校中实力最强的学科。
翟中和对于科学的发展有着卓越的预见能力和坚定的执着信念,对科学上的新东西有极大的兴趣,而且不怕付出任何代价。即使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他仍然坚持研究,充分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在有限的条件下做一些工作。科学的春天到来后,他又有新的想法,编写教材、建设学科,抓科学研究。
早在上世纪70年代翟中和就强调当老师必须做研究,只有搞好研究才能更好地服务教学。在当时很多老师不重视实验研究,但翟中和特别重视将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实验教学结合起来。把教学工作做好,并最终把教学经验积累起来,写几本能够影响一两代人的教科书,这是翟中和的一个理想,也是他的教学理念。
这个想法在上世纪80年代得以实施,1995年翟中和编写了《细胞生物学》一书,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印刷了9万多册,如今,《细胞生物学》已经再版了三次,平均每年销售5万册,有270个学校的专业和相关专业学生都在使用这本教材,是国内同类书籍中影响最大的,其中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的《细胞生物学》还获得了2002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奖一等奖。
翟中和的许多工作都围绕着北大细胞生物学科的发展和建设。他作为学科带头人,无疑是这个学科的核心。他不仅专注于自己的研究,更把大量的心血放在了学院、学科的整体发展上。翟中和还很重视对青年科研力量的培养,他常常教导自己的学生,提醒他们为年轻人的发展考虑,多注意对年轻人的培养,给还需要提高的老师多些支持、多些建议、多些帮助,让他们尽快成长起来。
124,我们共同的名字
2000年,70岁的翟中和仍孜孜不倦地工作着,一面为学校讲课、扶持地方院校的学科建设,另一方面,他当时担任着中国科学院学部常委、教育部生物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学位委员会副主任,并担任“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等的评审专家,其他的学术兼职更是难以计数。每天的繁忙让人总是以为他还是个年轻人。直到有一天,他出席完博士生答辩会后,走下楼梯时突然感觉天旋地转,同时不停地呕吐。被同事送到医院的时候,他已无法清楚流利地讲话,无法看清东西。经诊断,确诊为脑血栓。这之后的两年,他又因同样的病症先后住院两次。
翟中和现在已经不能亲自参加科研工作了,但他培养起来的学生现在“已经不是一支队伍,而是一个阵营了”。翟中和1978年开始招收第一批硕士研究生,1985年成为博士生导师,三十多年来共指导了80余名硕士生、博士生和博士后。现在他的学生中有10位在北大做教授、副教授,10多位在国内其他院校或研究所做教授、副教授。还有10多位在国外做教授、副教授或助理教授及杂志总编辑。还有几位任公司总经理或厂长。

1996年8月2日,学生们在实验室为翟中和院士(前排右二)庆祝生日。
这些学生团结在翟中和的身边。2007年,细胞生物学实验室被评为全国优秀集体,这个集体有个代号叫做“124”,124是他们朝夕相处、做研究工作共同使用的老生物楼的大实验室。一批批的学生从这里走出去,在海外他们写信回来总是深情地“问候124,怀念124”。这些学生从他身上学到的不仅是科学知识,更多的是勤奋、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教育学生的理念。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
涓涓师生情
焦仁杰 张传茂 陈建国 张博
在翟老师迎来八十大寿的时候,作为他昨日的学生,今日的同事,永远的朋友,我们深深地祝福他和杨老师身体健康、幸福长寿的同时,对一些深印在脑海的往事感觉有冲动想写下来与读者分享,以使这些故事可以影响更多的人,特别是让更多年轻的学子可以从中受益。同时也可以使年轻的科研工作者、年轻的PI们在遴选科研课题、处理与学生的关系等方面受到启发。
我们几个(张传茂、陈建国、焦仁杰、张博)当中,陈建国最早认识翟老师,不是因为他年龄最大,而是由于工作原因: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当很多中国人刚从“文革”的动荡中走出来还有点朦朦胧胧的时候,翟老师已经在病毒发生的规律以及病毒发生与宿主细胞关系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并且成为中国在这一研究领域的权威性专家。此时,在浙江农业大学就读硕士研究生的陈建国在电镜放射自显影实验方面遇到困难去信求助翟老师,很快得到翟老师的回信,并被接纳到北大生物楼124实验室学习该技术。翟老师手把手地传授超电镜技术,并亲自动手做了数天的超薄切片和电镜观察分析。在以后长达数年的合作研究工作中,翟老师给予的不仅仅是技术上的支持,更多的是在人生观和科学素质方面的言传身教。就这样,陈建国于1989年被吸引来到未名湖畔翟老师实验室攻读博士学位。同一年,张传茂也成了翟老师的博士研究生。当时翟老师更具前瞻性的思想是认为细胞生物学将是生命科学的前沿学科之一,因此他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就在北京大学成立了细胞生物学专业,并自己领导组织相关教学与科研队伍。他这一时期的研究已经将病毒的发生与细胞骨架(包括核骨架)的功能联系到了一起,并且应用的是当时很先进的研究技术:如整装分级抽提技术结合各种电镜技术,以及分子生物学技术显示中间纤维—核纤层—核骨架的细胞内网络体系的结构、成分与功能。焦仁杰和张博就是被他在这一领域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吸引到他实验室读研究生的。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翟老师与他的学生们还在实验室开辟了卓有特色、与时俱进的体外构建细胞核的研究。这期间,张传茂、蔡树涛、张博等直接体验、见证了翟老师勇于创新、永不驻足的科研精神。一个大雪皑皑的夜晚,时过10点翟老师才离开实验室。担心路滑,张传茂执意送翟老师回家。翟老师到了家门而不入,又执意送张传茂回实验室。这样来回三遭,他们边谈工作,边拉家常。颗颗雪中脚印,也印证了翟老师与学生的师生情谊。
翟老师对学生的爱护同时体现在科研与生活中,并且是科研与生活相结合。为了总是站在科学研究领域的前沿,同时也为了让自己的学生能最快地把握本领域研究的最新动向与技术,他先后将陈建国派送到世界上做细胞骨架最好的实验室之一——Hirakawa实验室做博士生联合培养;将张传茂派送到世界上最好的细胞核重建实验室之一 ——Clarke实验室做博士后研究;将张博派送到美国科学院院士HansRis实验室学习当时非常先进的高分辨率低压扫描电镜技术,这项技术对当时翟老师实验室的核重建课题很重要;翟老师在上世纪90年代初除了强调细胞生物学在生命科学领域的重要地位之外,开始深深意识到生物学研究最终要解决的问题是发育生物学的问题,于是他于1994年派送当时硕士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的焦仁杰去知名的果蝇分子遗传与发育生物学实验室——M.Noll实验室攻读博士学位。
翟老师对科学研究新趋势的高度敏感还可以从以下几件“小事”中体现出来:1995年10月份,每年一度的诺贝尔奖揭晓,当年生物医学奖授予了对揭示果蝇早期胚胎发育遗传调控规律作出重要贡献的ChristianeNüsslein-Volhard、EricF.Wieschaus和EdwardB.Lewis三位科学家。翟老师在第一时间便联系上当时正在苏黎世大学从事果蝇分子遗传发育研究的焦仁杰,请他将这一消息写一个中文介绍(评论)在国内发表,以使国内的科研工作者、青年学生在第一时间了解相关内容。记得当时在中国从事果蝇分子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的同事几乎为零。当今在国内从事相关研究的实验室已四五十个。这是中国生物学研究15年来的巨大变化之一。也是在1995年底、1996年初在焦仁杰从苏黎世回国探亲时与翟老师的一席谈话中深深感觉到翟老师对当时生物学研究前沿的把握,他当时深深意识到细胞内信号转导在机体发育过程中的调控作用。
翟老师对他的学生们关怀还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焦仁杰上研究生的第一年因为身体原因休学一年。此后,在实验室翟老师见面后问的第一句话总是身体怎么样,然后才是工作上的事情。张博生了孩子后,翟老师亲自去医院和家中探望,工作繁忙时也要委派实验室的年轻人代为问候。张博在瑞士进修期间,她的父亲突发脑溢血,翟老师竭尽全力联系安排住院,赢得了宝贵的治疗时间。类似的关怀之情不胜枚举。翟老师对学生们的生活关心备至,但是却很少对自己的工作与生活条件斤斤计较。翟老师的实验室曾经数次易址,仅我们做学生时就经历过从老生物楼310到124、再从老生物楼124到生命中心306的变迁。当然,每一次变动都伴随着实验条件与工作环境的改善,但是,翟老师却始终没有为自己争取一间独立的办公室,总是跟学生“打成一片”,即使是当选为院士之后他的办公桌也依然摆放在实验室的一角,直到2003年生命科学院大部分科研实验室整体搬迁到新落成的金光生命科学大楼,大部分PI都有了独立的办公空间之后,翟老师才“入乡随俗”,有了专用的办公室。
总之,翟老师对他的学生的关怀可谓是无微不至,在我们成为老师之后翟老师仍然把我们时刻挂在心上,依然关心着我们的每一步成长。就像做了父母之后才会更深刻地懂得父母对儿女之爱的无私与伟大,我们在自己有了学生之后更加深深体会到翟老师对我们全方位的关爱与付出所饱含的深情厚谊。这种师生情谊曾经在许多重要的时刻陪伴着我们,给我们以不可替代的力量;这种师生情谊还会继续激励我们不断进取,激励着我们用勤奋和努力来回报这不求回报的关心与爱护。
(作者单位:焦仁杰:广州医科大学;张传茂、陈建国、张博: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