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的1918年9月11日的下午,正是美国东北部的历史文化名城波士顿最美的秋天,一个来自中国的青年吴宓悄然抵达剑桥,开始了其在哈佛大学为期四年的留学生活。这是一个看上去极为平淡无奇的秋日午后,落英缤纷的街道安静得让人神定气闲,一战即将结束,世人正从战时的情绪缓慢调整到日常的节奏之中。但借由吴宓当年留下的日记所呈现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却可以发现以吴宓为参与者和见证者的这一群一战前后聚集在哈佛的中国留学生(赵元任、梅光迪、竺可桢、李济、陈寅恪、汤用彤、张鑫海、林语堂、楼光来、顾泰来等)超凡脱俗,如此不同凡响,用群星闪耀来描述也不为过。纵览近代中国的留学史,可谓是空前绝后的一代“文化贵族”(吴宓语),让人不得不感慨“天才为何总是成群地来”。

吴宓
吴宓是近代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怪才,是一个典型的矛盾体。他自身的存在充满了一种悖论,他所向往的人格往往是其极度匮乏的,他反对的行为方式往往又是他一边抱怨一边在实践的。他在哈佛时生活在梅光迪、陈寅恪和汤用彤的巨大阴影(并无贬义)之下,后者的学识、德性与才华让吴宓赞叹和歆羡不已。或许正因为此,吴宓的一生都只能扮演一个高端学术的鉴赏者,一流学者的知己和引荐人(比如力荐陈寅恪执教清华国学研究院)而无从作出自己独特的学术贡献。即使是他一生迷恋的古体诗词,也被胡适在日记里骂为“烂诗”,余英时先生也认为吴宓其实并无特别的诗才。可是我们却不能轻易地指责吴宓是一个知行分裂的两面人,他是一个软弱而倔强的性情中人,从其之后的人生历程来看,吴宓几乎从未屈服于外在的权力压迫和思想规训,他与陈寅恪仿若那个黑暗时代的双子星座,虽然微弱而摇曳不定,却毕竟给了后世治史者些微的光亮。尤有进者,众所周知,同龄人甚至同代人之间最难相处,尤其是处身于同一个领域而都需要崭露头角的知识人。自诩为新人文主义精神领袖白璧德中国传人的吴宓诚然一生对新文化派如胡适、陈独秀等人心怀不满,语近谩骂,但对于他在哈佛往来最多的学者如陈寅恪、汤用彤等,却是心悦诚服一生不变的,敬重前辈或激赏后学都不难,难的是对于同代人中才华横溢或学术出众者持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欣赏,并且毫不难为情地求教,或者毫不吝啬地援助。吴宓虽然没有多少思想学术的原创性和文学的才华,但其一生将记日记当作人生事业来坚持,巨细靡遗地记录了他所栖身的20世纪中国知识人社群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并且以其实际行为践履了他最欣赏的陈寅恪推崇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这一价值准则。仅此一端,也足以载入史册。
在波士顿郊区剑桥的寒冬午后,轻轻打开吴宓写于一百年前的留学日记,读着这些或长或短的字句,以及在字里行间跃动的生命体验与纷繁思绪,仿若跟随一个从遥远中国走出来的青年知识人在波士顿城区和哈佛校园步履匆匆,重新经历了他在哈佛的生活与思想,由此也可以管窥聚集在波士顿的这个独特留学生群体的历史面相。这真是一次奇幻的历史文化之旅。从吴宓日记来看,他所穿梭其中的这个留学生群体大都术业有专攻,有各自的学习和研究特长,并且能够沉浸其中。吴宓伸展出他的敏感而细腻的触角,从这些同辈人中汲取新知和人格的力量。陈寅恪是1919年1月29日抵达哈佛所在的剑桥,未几就经由其表弟俞大维认识了先前到此地的吴宓,两人可谓一见如故,成为终生挚友。3月2日吴宓在哈佛中国学生会演讲《红楼梦新谈》,陈寅恪赠诗一首《红楼梦新谈》题辞:“等是阎浮梦里身,梦中谈梦倍酸辛。青天碧海能留命,赤县黄车更有人。世外文章归自媚,灯前啼笑已成尘。春宵絮语知何意,付与劳生一怆神。”自此以后,陈寅恪在吴宓的哈佛日记里频频出现。同年3月26日,吴宓在日记中写道:“陈君学问渊博,识力精到。远非侪辈所能及。而又性气和爽,志行高洁,深为倾倒。新得此友,殊自得也。”无论是学术还是人格,陈寅恪都成了吴宓景仰的对象,从这简短的语句可见吴宓人生得一知己的难以自抑的欢愉与兴奋。就连吴宓购买西文书籍,也是得陈寅恪等提醒,而开始搜购收藏以备回国后教研之需。吴宓1919年8月18日日记写道:“哈佛中国学生,读书最多者,当推陈君寅恪,及其表弟俞君大维。两君读书多,而购书亦多。到此不及半载,而新购之书籍,亦充橱盈笥,得数百卷。陈君及梅君,皆屡劝宓购书。回国之后,西文书籍,杳乎难得,非自购不可。而此时不零星随机购置,则将来恐亦无力及此。故宓决以每月膳宿杂费之馀资,并节省所得者,不多为无益之事,而专用于购书,先购最精要之籍,以次类及。自本月起,即实行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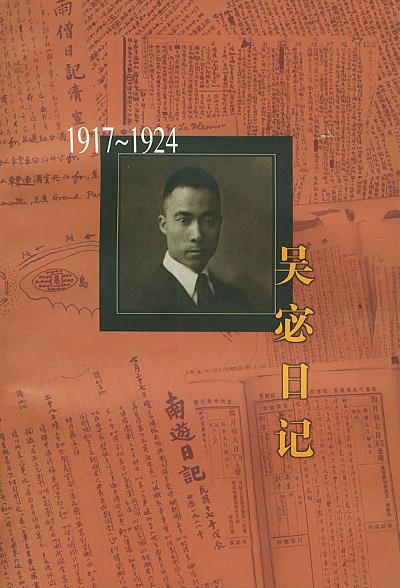
《吴宓日记(1917-1924)》
4月25日,吴宓在日记里写道:“近常与游谈者,以陈(陈寅恪)、梅(梅光迪)二君为踪迹最密。陈君中西学问皆甚渊博,又识力精到,议论透彻,宓倾佩至极。古人‘闻君一夕话,胜读十年书’,信非虚语。陈君谓,欲作诗,则非多读不可,凭空杂凑,殊非所宜。又述中国汉宋门庭之底蕴,程、朱、陆、王之争点,及经史之源流派别。宓大为恍然,证以西学之所得,深觉有一贯之乐。为学能看清门路,亦已不易,非得人启迪,则终于闭塞耳。宓中国学问,毫无根底,虽自幼孜孜,仍不免于浪掷光阴。陈君昔亦未尝苦读,惟生于名族,图书典籍,储藏丰富,随意翻阅,所得已多;又亲故通家,多文人硕儒,侧席趋庭,耳濡目染,无在而不获益。况重以其人之慧而勤学,故造诣出群,非偶然也。”吴宓在这则日记里分析了陈寅恪有过人之见识的来由,除了指出陈寅恪的勤奋与聪慧外,他认为陈出身世家名族也大有关系,耳濡目染之际,往往得潜移默化之果。同样出身书香门第的已故旅美学者林同奇在《林氏家风:中国士大夫传统现代转化一瞥》所作的家族史记录也可以例证吴宓这一见解。相形之下,吴宓对自身越来越不满意,基本上是否定性的负面评价,而其回国后的公共人格表现出来的却又是一种极其自负、睥睨众生的特质。吴宓认为家族、阶层出身对个人治学的底蕴与眼界有莫大关系,这一观点也是他一直贯彻始终的。到了抗战后期的1943 年2月15日,吴宓在为陈寅恪父亲陈三立撰写的《读散原精舍诗笔记》中由衷写道:“先生父子(指陈宝箴、陈散原父子),秉清纯之门风,学问识解,惟取其上,而无锦衣纨绔之习,所谓‘文化之贵族’,非富贵人之骄奢荒淫。降及衡恪、寅恪一辈,犹然如此,诚所谓君子之泽也。先生少为‘四公子’之一,佐父首行维新改革于湘中,坐是黜废禁锢,而名益显,望益高。所与交游倡和者广而众,又皆一世之名士学人、高才硕彦。故义宁陈氏一门,实握世运之枢轴,含时代之消息,而为中国文化与学术德教所托命者。寅恪自谓少年勤读,盖实成于家学,渊孕有自。而寅恪之能有如斯造诣,其故略如宓以上所言,非偶然者也。”精英文化的浮沉往往系于世家大族的兴衰荣辱。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也曾经论及这一点:“纵览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气之变迁有关。当其新旧蜕嬗之间际,常呈一纷纭综错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斯诚亦事实之无可如何者。虽然,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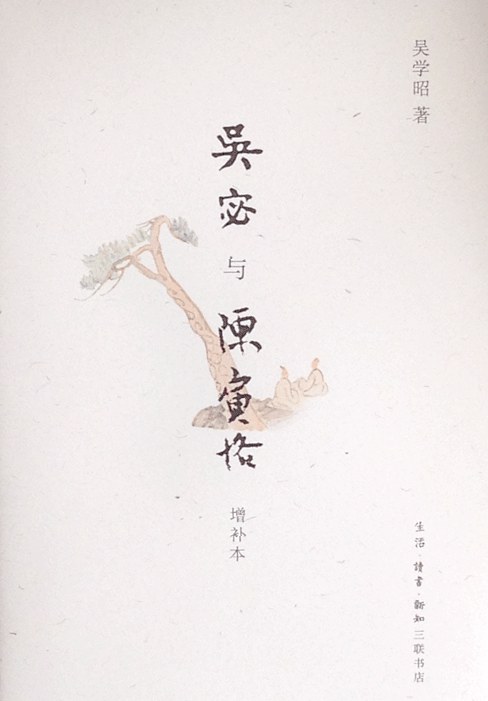
《吴宓与陈寅恪(增补本)》
吴宓的女公子吴学昭也曾在《吴宓与陈寅恪》一书中写道:“听父亲说,昔年在哈佛,志同道合,情趣相投,往来密切的同窗好友,除了寅恪、锡予伯父,梅光迪和俞大维先生,还有张鑫海、楼光来和顾泰来等君。父亲常夸清华一九一八戊午级毕业同学张鑫海(后改名歆海)‘年少美才,学富志洁,极堪敬爱’。张君浙江省海宁县人,英文优长,从白璧德师学,得文学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马修·阿诺德的古典主义》(The Classicism of Matthew Arnold)。又说清华一九一八级毕业同学楼光来英文极好,入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一年即得文学士学位,升入哈佛研究院治文学,成绩亦佳,‘为人严正,甚重道德’。顾泰来君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英文也极好’,一九二〇年初春自费来哈佛习历史兼政治。与父亲和锡予伯父相识,遂成为知友。‘三人每日同餐,同游,同出入,同研究校课,形迹极密,心情亦厚。’父亲说,诸君多具有深厚的国学基础,对西方文化也相当了解,在对待祖国传统文化的问题上,不赞成胡适、陈独秀等的全面抨击、彻底否定、破旧立新,而主张昌明国粹,融化新知,重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继承性,在现有的基础上完善改进。又说当时在哈佛习文学诸君,学深而品粹者,均莫不痛恨胡、陈。张鑫海表示,‘羽翼未成,不可轻飞。他年学问成,同志集,定必与若辈鏖战一番’。”如此情怀,亦可理解,受白璧德影响对中国文化传统深怀敬意与温情,试图昌明国粹,融化新知,而远在大洋彼岸的故国却已然陷溺在欧风美雨对传统的摧折之中,支撑中国文明的儒家传统摇摇欲坠,近乎两头不到岸的孤舟游魂。这种悲情意识与文化托命的自我认同形成了一种强固的心灵结构,既有共同的敌人,又有彼此抱团取暖的知己,并且有来自白璧德等哈佛名师的加持,也就不难理解吴宓此时此刻的心志,以及张鑫海的“鏖战”一词。其时与吴宓合租一房每日相往还的汤用彤也主张面对西方应该改变出主入奴之态度,培养独立反省之文化,不降志,不辱身,不媚外。他在一篇后来刊于《学衡》的文章中说道:“今日中国固有之精神湮灭,饥不择食,寒不择衣,聚议纷纷,莫衷一是。所谓文化之研究,实亦衰象之一。菲薄国学者,不但为学术之破坏,且对于古人加以轻谩薄骂,若以仇死人为进道之因,谈学术必须尚意气也者。……主张保守旧化者,亦常仰承外人鼻息,谓倭铿得‘自强不息’之精神,杜威主‘天(指西方之自然研究)人(指东方之人事研究)合一’之说,柏格森得‘唯识’精义。……盖凡此论者,咸以成见为先,不悉其终始,维新者以西人为祖师,守旧者借外族为护符,不知文化之研究,乃真理之讨论,新旧淆然,意气相逼,对于欧美,则同作木偶之崇拜,视政客之媚外,恐有过之而无不及也。”
有趣的是,这明明是一个抱团取暖的留学生群体,吴宓却常常强调自身不肯为主义或流派所规定的自由心志,这也恰恰说明了吴宓极其矛盾的心态。吴宓在留学哈佛日记中曾写道:“吾自抱定宗旨,无论何人,皆可与周旋共事,然吾决不能为一党派一潮流所溺附、所牵绊。彼一党之人,其得失非吾之得失,其恩仇非吾之恩仇,故可望游泳自如,脱然绝累。此就行事言之也。若论精神理想一方,吾自笃信天人定论、学道一贯之义,而后兼蓄并收,旁征博览,执中权衡,合覆分核,而决不为一学派、一教宗、一科门、一时代所束缚、所迷惑;庶几学能得其真理,撷其菁华,而为致用。吾年来受学于巴师,读西国名贤之书,又与陈、梅诸君追从请益,乃于学问稍窥门径,方知中西古今,皆可一贯。天理人情,更无异样也。此‘无所附丽’之又一解也。总之,吾但求心之安,逃于忧患。凡此种种,皆暂不弃世而图自救之术耳。”其时的吴宓,面临着严峻的精神危机,曾试图到查尔斯河自绝于世,对自我严苛的要求,近似于一种道德圣徒的境地,同时对自我学术也有极为崇高的期许,而日常生活中的吴宓却常常被世俗琐事甚至隐蔽的情欲所牵绊,读其日记感觉他每天都在疲于奔命,成了一个不会拒绝别人的意志软弱的人,比如为了婚事常与家人以及未婚妻陈心一的亲人反复通信沟通,比如接待从各种途径到访波士顿的师友,迎来送往,参与编辑约稿,哈佛中国学生会的活动等等分割了他很多的时间与精力。尤有进者,自青年时代起,他既得益于与梅光迪、陈寅恪、汤用彤等一流学人的谈史论学,开阔了眼界,培养了见识,可也被笼罩在梅、陈等巨星之下,尤其对陈寅恪近乎学术粉丝心态,自成一家的学术主体性并未得以确立,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或许正因为此,畏友陈寅恪或汤用彤在哈佛同学时对吴宓的批评,每每让其既警醒,又耿耿萦怀而欲自辩。陈寅恪言及婚姻与人生之关系事,取豁达自然通透之态度,而每批评吴宓之泥足深陷、难以自拔之作茧自缚,而对于学术自由与人格独立之关系,陈更是有着清醒的认知,没有吴宓身上那一种夹缠不清的书呆子气。1919年6月3日,吴宓在日记中记载陈寅恪的话,“‘学德不如人,此实吾之大耻。娶妻不如人,又何耻之有?’又云‘娶妻仅生涯中之一事,小之又小者耳。轻描淡写,得便了之可也。不志于学志之大,而竞竞惟求得美妻,是谓愚谬。今之留学生,其立言行事,皆动失其平者也’”。这可能是针对留学生群体习染欧风美雨,倡导恋爱神圣之说,每每单方面撕毁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预定之婚约,而欲在女留学生中选择新式女子之风气。胡适在1918年9月写成的《美国的妇女》一文里对此也有严厉的批评:“近来留学生吸了一点文明空气,回国后第一件事便是离婚。却不想想自己的文明空气是机会送来的,是多少金钱买来的。他的妻子要是有这样的好机会,也会吸点文明空气,不致受他的奚落。……这种不近人情的离婚……是该骂的。”而对于经济独立与学术自由之关系,陈寅恪也有深刻的论断。吴宓在1919年9月8日的日记里记载陈寅恪的言说:“我侪虽事学问,而决不可倚学问以谋生,道德尤不济饥寒。要当于学问道德以外,另求谋生之地。经商最妙。Honest means of living。若作官以及作教员等,决不能用我所学,只能随人敷衍,自侪于高等流氓,误己误人,问心不安。至若弄权窃柄,敛财称兵,或妄倡邪说,徒言破坏,煽惑众志,教猱升木,卒至颠危宗社,贻害邦家,是更有人心者所不忍为矣。”学问不足以谋生,而经济独立才是人格独立的前提之一,这论断放在当今中国之学界,也同样适用。
无独有偶,同居一室的学友汤用彤对吴宓也偶有严苛之批评,给吴宓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尤其是对吴宓热衷交际、荒疏学问的指控,让吴宓久久难以释怀。吴宓其实并无长袖善舞之潜质,却又跃跃欲试于交际场合,所以真是有点用非所长自取其辱。据吴宓日记(1919年12月29日)所记录,“近宓常有此感,但惜宓于诸学之藩篱,尚未尽涉耳。留美同人,大都志趣卑近,但求功名与温饱;而其治学,亦漫无宗旨,杂取浮摭。乃高明出群之士,如陈君寅恪之梵文,汤君锡予之佛学,张君鑫海之西洋文学,俞君大维之名学,洪君深之戏,则皆各有所专注。宓尚无定决。文学与报业,二者究将何择,久久不决。现拟暂不明白划分,而乘时多读佳书,无论其为文学、历史、政治、时局、哲理等,但能选择精当,而所读既多,必有实益。且此心得安,则精神舒适,纵有琐屑烦恼,皆不足计较矣。凡学问事功,均须下苦功,未有不耕耘而收获者。锡予言,‘宓在清华时,颇有造成学者之志趣,之气度。及民国五六年间,在校任职一年,而全失其故我。由是关心俗务,甚欲娴习交际,趋重末节,读书少而心志分,殊可惋惜’云云。按宓近今之见解,以为人生应有之普通知识,及日用礼节规矩,例应通晓,且习之亦不必即害正业,故亟欲一洗前此偏僻朴陋之病,非有从俗学交际之心。且生来本无此才也。惟锡予既如是言之,复除亦尝有讥讽之意;是诚我之大缺失,亟宜改省”。吴宓自辩为欲借此一改中国读书人固有的书呆子气,却得不偿失,反而为友人所讥笑,以为他热衷于俗务倾心于应酬,就此而言,或许才能理解吴宓以读书来自我救赎获取内心安宁的“读书教”之所由来。读书写日记就成了吴宓的一种具有宗教仪式感的行为了!友朋学问日进,而自身几无寸功,吴宓自然就容易滋生沮丧愧疚之心情。他曾在日记里吐露心声道:“张君鑫海年少美才,学富志洁,极堪敬爱。此间除陈君寅恪外,如锡予及张君鑫海,及日内将到此之楼君光来,均具实学,又极用功;在今已为中国学生中之麟凤,其将来之造诣,定可预知。学然后知不足,学愈深,愈见得自己之所得者尚浅。故如锡予与张君等,均又实心谦虚,尤足称道。宓于学问,毫无实功,今即与二君较,远不能望其项背;而年华已长,忧国伤乱,魂梦不安,又为种种邪魔杂念所侵扰。静中回首,虚靡之光阴,真不为少。欲纯静潜心用功,实难之又难,将来只可以常人终身。吁!可惊也,可伤也。”
不过这是吴宓在哈佛中国留学生群体的内部比较时所形成的自伤自哀情绪,所谓同辈皆如群星璀璨的天才,而自己却才疏学浅,心志不坚,邪魔杂念缠身,安身立命无所寄托。而当他在日记里写到纽约的中国留学生群体时,则自身属于波士顿或者哈佛留学生群体的一种自我肯定、鄙视纽约留学生的认同就遮掩不住地显露出来。一言以蔽之,在吴宓的笔触之中,剑桥才是追求真知、潜心读书之所在,而纽约这个花花世界却成了腐蚀中国学生、毒化其心灵的城市。据其1919年9月4日的日记记载,“午后,杨孟纪来,复述在纽约所见中国留学生情形。若辈各有秘密之兄弟会,平日出入游谈,只与同会之人,互为伴侣。至异会之人,则为毫不相识,虽道旁见值,亦不头点招呼。其专门职业,共有二种,而读书为学不与焉。凡在纽约读书者,均只挂名校籍,平日上课,亦或到或不到。该处学位既亦取得,考试又皆敷衍,故无以学问为正事者。其二种职业为何?(一)竞争职位。结党营私,排挤异党之人。而如学生总会、年会之主席、会长等,及《月报》《季报》之编辑、经理等,必皆以本党之人充任,不惜出死力以相争,卑鄙残毒,名曰‘Play Politics’。而国事及公益事业,则鲜有谈者,更安望其实力尽忠耶?(二)曰纵情游乐。无非看戏、吃饭、跳舞、狎妓等事,而日常为之,视为正业。于是奢靡邪侈,无所不至。平日相聚吃饭,或有请宴者,则必男女偕来,每一人柬招一女留学生,(谓中国女学生,其在纽约者,皆甚不高明)入席则并肩坐。其情形酷类中国之招妓侑酒”。仅过三日,他又在日记中写道:“昨记纽约中国留学生情形,而波城(康桥附近)之留学生则大异。波城及其附近,亦有留学生百馀人,然大率纯实用功、安静向学者居多。在留美学界中,要为上选。(哈佛及麻省理工学院,课程亦较严,迥非纽约哥伦比亚等校之比。)而纽约之中国学生,则鄙夷之。谓凡来波城读书者,皆愚蠢无用之人,不如彼辈之活动能事云。”纽约与剑桥,形成了民初留学史上风气迥异、彼此仇视的两个星团,孰是孰非,有待留学史专家进一步的考证。就我的阅读体验而言,聚集在哈佛、麻省理工的中国学生确实更为笃学自律一些,其后来的学术与文化成就更是学界公认、有目共睹。
王汎森曾在一篇短文《天才为何成群地来?》中谈及19世纪欧洲思想之都维也纳,正是“天才成群地来”的地方。维也纳城大量的咖啡馆成为繁星们的养成之所,往往体现了一群人如何把一个人的学问及思想境界往上“顶”的实况。当时维也纳的小咖啡馆,点一杯咖啡可以坐一天,甚至信件可以寄到咖啡馆,晚礼服也可以寄放在那里。譬如维也纳的格林斯坦咖啡馆(Cafe Grien-Steidl)就有包括茨威格等大人物。以此对照一百年前聚集剑桥的中国留学生群体,真有异地而同时之感,他们在此地风云际会地相遇相识,甚至相守一生,读书、交谈、思考、写作,逛书店,喝茶,吃中国餐馆,修课,求索中国文明的奥秘与出路,真正达成了学术生涯与心灵生活的高度契合,这是一个近代中国留学史上严重被忽略的群体。按照余英时先生的看法,这个群体确实很特殊,此前没有,此后也再没出现过,而这个知识群体面对中西学术与文化所展现的襟怀与抱负,尤其是其中大部分的成员不以区分中西新旧为心魔,自由涵泳往复于多元的学术文化传统之中的态度,直到今天仍旧有其启示价值。而一生虽然学术上无大成就的吴宓,却以其文人的细腻敏感和学者的严谨,巨细靡遗地记录了哈佛中国留学生的这个“黄金时刻”,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见证和学术的备忘录,对于今人在众声喧哗的时代格局中探索中国文化的由来与归途更是具有深远的启示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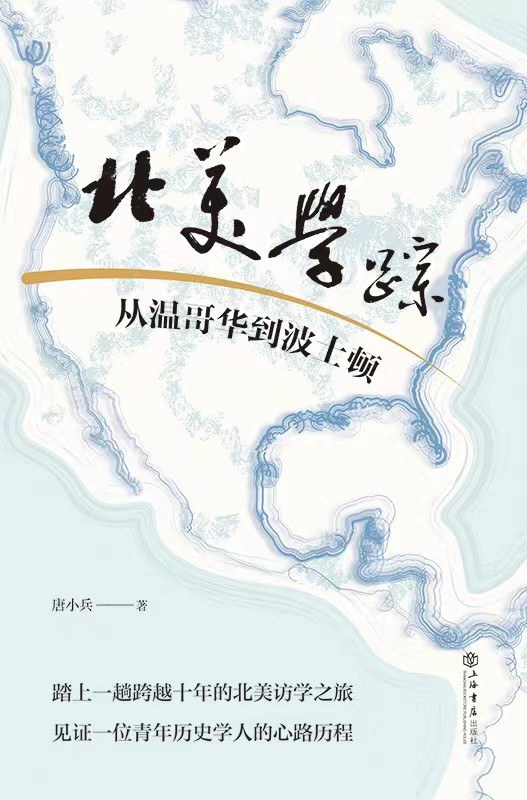
本文选自《北美学踪:从温哥华到波士顿》,唐小兵 著,上海书店出版社|也人,2022年6月版,澎湃新闻经出版社授权摘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