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星,清华大学建筑学院2003级本科生,2007级硕士,Harvard GSD硕士。拥有在美国、丹麦、荷兰等多个国家的实践经验,曾在都市实践、BIG、UNStudio、KPF等多家国际一流设计公司工作,曾任纽约KPF高级建筑设计师。2016年在纽约创建XING DESIGN工作室,2017年入驻上海,注册为“行之建筑工作室”。

两年前,我辞去纽约的工作空降上海创建工作室。没有缓冲,没有挂靠,从零开始。这意味着学历和履历没法像求职那样直接变现,只能靠实力一步一步往前走。
校训有云"行胜于言",工作室就叫“行之”吧。

2018年工作室搬到了陕西南路,对面是巴金故居。看着弄堂里的被子裤衩,仿佛也更接地气了一些。
这个时代提出了很多崭新的命题,但建筑学科似乎被圈内描述得陈腐封闭。好像学建筑的都要完蛋了——不转行都不好意思给人打招呼。
但我心目中的建筑绝不是陈腐封闭的。
建筑既不是舞台表演昙花一现,也不是手机触屏上的平面内容,更不是虚幻的交易,建筑设计在实实在在的塑造“日常存在”的三维空间。甚至该这么说:和生活空间相关的,都是建筑的范畴,它是各个领域和学科的接口。只要怀有塑造生活空间的意愿,嫌弃无聊,向往有趣——不论是上海的弄堂里还是拉格朗日点上——建筑设计都有无限的可能性。

前些年的高速城市化发展,给我们带来了千篇一律的城市,道路(而不是街道),电池盒子一样的楼房——这些其实只是抗通胀的对冲基金。市场这么聪明,行业上总结出各种套路和技法,既高效又省事儿,不仅把建筑搞得无趣,也把生活变得乏味。不过好在,这些套路逐渐吃不开了,生活需要多样性的回归。独立建筑实践,是热爱生活最直接的方式。
我们目前的项目主要有三类:有一些是其他人不愿啃的骨头——或经典套路失效,或限制太大而不知所措的;另外一些是不确定,需要自行命题的;还有一些是需要和多媒体交互,机械,数字技术相融合的。也正因如此,我们得琢磨来龙去脉,反思约定俗成,尝试另辟蹊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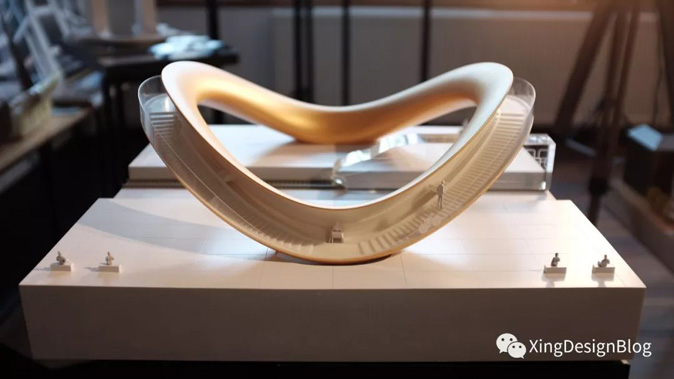
在开业之前,我敬仰出众,鄙视平庸的依据是,有精彩的设计想法。后来我意识到,好的事务所必须具备两种才能:首先是设计的核心天赋和实力;更重要的是足够长的血槽:被各种琐碎的事物损耗之后,仍留有旺盛精力投入设计本身。
“去做有趣的事情”不是一个选择,而是一种能力。
Bjarke以前常说,建筑就好像要把100项任务全部完成,一项不达标就会导致变质——换言之只要阻挠了其中任一项,你就失败了。就一个项目而言,没有迭代的机会。捣乱因素有很多,有很多是不可控的。这意味着付出不一定有回报。当然还有更多的烂事儿使你陷入失望和恐(饥)慌:例如内耗导致前功尽弃;关键时刻被放鸽子釜底抽薪;起初豪言壮语,最后不了了之甚至拖欠款项等等。
不要因为这些境遇(仅仅)变得更会骂街,要更冷静,别让挫折感吞噬创造力。

令人欣慰的是,总体上大家的品味其实越来越好,用不着迎合假想出来的“低俗审美”。也许他们一时不知道想要的是什么,直到你呈现在他面前的东西好到足够说服他。影响设计的因素很多,而自己的认可也许是最重要的——自己都觉得没劲的东西,怎么说服别人去接受呢?
虽然设计不是项目成功的全部,但好的设计确实有煽动性的,能极大增加实现的可能性。我们好几个项目是以设计力挽狂澜一锤定音。越来越多的人也明白了,随便做做的玩意儿,也多半成不了。
我们的绝大部分业主和合作方都非常棒,非常感激他们。我们也有幸遇到了几位伯乐,在合作过程中增进了解,相互碰撞,共同挖掘设计的价值。

在实际的工作中,时间和效率最重要。只有目标清晰,方法得当,配合紧密,才能节省出更多的精力放在设计本身。低效的加班是没有用的,浪费时间就是自杀。
浪费时间的方式包括:纠结犹豫(你没有分辨好坏的能力么),无效的多方案比较(如果全是垃圾,怎么选都是垃圾),理解错误(跑题了怎么做也是不对的),低级错误(返工花双倍的时间,相当于死两次),误差积累(早晚得重新来过,不如一开始就精确一点),不会做(一天做不出来,冥思苦想一星期也没用,不会就得先学)。

最后,我要感谢团队。不论时间长短,职位如何,每个人都工作在设计的第一线,遵循我定制的严苛的工作方法(包括对使用软件的操作流程)。工作的过程高强度,高效率,要学习的新东西很多。大家一边被我虐,一边一起创造有意思的东西,和工作室一同成长。
一眨眼两年过去了,虽然充满艰险,但总体是激动人心的。就像在海里游着,当然得时刻面对鲨鱼和风暴,但毕竟你也拥有海洋的广阔。
2018.1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