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 我们去看烟火
看那
繁花之中如何再生繁花
梦境之上如何再现梦境
我们并肩走过荒凉的河岸仰望夜空
生命的狂喜与刺痛
都在此刻
宛如烟火”
--席慕容
一转眼从清华毕业快二十年了——弹指一挥间的二十年,清华永远停留在青春的记忆中。
我是1996年进入环境系的,2000年进了“编双”。毕业后,在一个教对外汉语的机构工作。下班以后,常和同事去南门外一个叫“雕刻时光”的咖啡馆,点几盘精致的小点心,喝喝咖啡,聊聊闲天,半天就打发过去了。在那里常常能碰到学生,有的是去学汉语,有的纯是为了消遣,跟我们打过招呼以后,就坐在咖啡馆的一角静静地看书写字或者低声地和朋友聊天。坐在那里,能感觉到时间静静地流淌,不疾不徐、从容不迫地。一层玻璃便把喧嚣的市井隔在外面——要是时间能定格在这一刻,该有多好?
对清华的记忆是不连续的片段,我把它们拼拼补补,试图凑出一个完整的图像。
五号楼
环境系的女生住五号楼二楼。楼上、楼下是生物系和中文系的女生。五号楼前有个小卖部,一年四季卖应季的零食和水果。虽是个不起眼的小门面,生意却异常红火。夏天,常有三三两两打球回来的男生,热气腾腾地冒着汗,买一个西瓜,在旁边的石台上摔开了坐吃,一边貌似不经意地打量着过往的男男女女。这条路上的人总是络绎不绝:有的拎着暖瓶去打开水;有的从食堂打饭归来;最惹眼的是从公共浴室回来端着脸盆的女生,头发湿漉漉的,有说有笑地经过,空气中便弥散着洗发水的余香。
五号楼对面是九食堂。九食堂的汽锅鸡、煎鸡蛋是令人难忘的美食。煎鸡蛋的师傅是个人物。虽然煎鸡蛋这样一个简单的动作每天要重复几百遍,他也能做得充满仪式感。鸡蛋煎好,便甩开一条油光水滑的嗓子吆喝一声“煎~~~鸡蛋!”便有人应声从人群中挤出来,把煎好的鸡蛋端走。在食堂吃饭,可尝到天南海北的口味,亦可欣赏各色人等。一次看到一个女生,一根筷子上戳着两个大白馒头,边走边吃。吃法之豪迈,叹为观止。
因为是女生楼,每天出入五号楼的都是衣着光鲜亮丽的女生,男生是不许入内的。于是总有痴心的男子拿着鲜花在楼外苦等,或是抱着一把吉它在窗下轻轻地弹唱,希望他心仪的女生能够听出这歌中的意思。晚上十一点熄灯以后,楼门便上了锁。时常有女生被锁在外面,在寒风中苦苦哀求宿管阿姨,百般解释,方得放行。
楼门口种着一排银杏树,下面摆着两张长木椅,总有人在那里谈情说爱。坐在椅子上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银杏树却依然如故:春天,树叶抽出嫩绿的新芽;秋天,树叶变得金黄,也许是一阵凛冽的秋风,一晚的功夫,树叶便落满了地面;来年,春回枝头,周而复始。
室友
大学的时候四个人住一个宿舍。我有三个室友:江苏的小宁,内蒙的阿清,山西的小禧。我最大,阿清其次,小宁和小禧比我小两岁。有一次,我们四个人结伴去南门外的一个机构面试兼职工作,面试官拿着我们的身份证说:“你们是一级的吗?”
我们四人常常同出同入,宛如四胞胎。金工实习的时候,我们穿着统一发放的靛蓝色工作服,戴着白色的工作帽,俨然四个国营企业女工。午饭后,便一同骑着自行车,穿过法国梧桐掩映下的主干道,拐到一条偏僻的小路上,再骑几分钟,便到了实习车间——这个下午,不知道又有多少个报废的零件要被生产出来。

作者为前排右二
四个人中,我是生活上最不拘小节的。因为家住北京,常常攒了一周的脏衣服,周末拿回家洗,周一再带了干净衣服来。因为不会叠衣服,就散乱地堆放在衣柜里,一开柜门,衣服能喷涌而出。
那时候,每个女生的床上都有床帘,睡觉或者做点“隐秘”的事情时,就要拉上。对床帘的花色选择反映了女生的小情趣。我时常躲在床帘里看海子的诗。其余的三个室友的床帘平时总是拉开的,露出收拾得一丝不苟的床铺,保留着军训的遗风。挨着床铺的两面墙壁都用大白纸裱糊得严丝合缝。正对面的墙上钉着一个三层的白漆皮钢丝书架,上面永远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几本专业书、英文书和消遣用的小说,除此之外,还有几件女孩子喜欢的小装饰品、搽脸油什么的。那时候宿舍里流行这种书架,东西多的人甚至会钉三四个,把自己的空间挤得小之又小,睡觉时几乎不能翻身。在上铺铺床叠被颇需要技术,因为一个人得屁股坐在铁栏杆上,半个身子悬在空中收拾,还得爬来爬去,方才把一张床收拾停当。
小禧是山西人,说话慢条斯理的,有点囔囔鼻儿。她家乡的很多说法翻译不成普通话,所以她就硬生生地用普通话说老家的方言。有一次,我问她借自行车。她把我引到窗口,指着楼下一排满满当当的车说,“就是那个有红坐墩(墩发得有点鼻音,又像“蹬”)的。”我一愣,然后很快明白了她的意思,扑哧一笑,说“什么是‘坐墩’啊?”她就不好意思地笑笑说:“不知道普通话怎么说,在我们家乡是叫‘坐墩’的。”
小禧有睡午觉的习惯,一到十二点半,床帘就拉上了,于是一屋子的人就知道应该轻手轻脚地活动,不要打搅她。她有时候一觉睡很长时间,然后猛地惊醒,不知身在何世的样子。坐在床上迷迷瞪瞪一会儿,揉着眼睛说:“睡噎着了。”我只听说过吃饭吃噎着了,从未听说过睡觉睡“噎”着了的。小禧说这是她们那儿的方言,睡得不舒服,做恶梦,还醒不过来,就叫睡噎着了,普通话里恐怕没有这个字。我后来看书,发现这个“噎”可能是“梦魇”的“魇”字。
小宁是有名的学霸,门门功课都优秀,唯独建筑制图课总是受挫,自己矜矜业业画的线条总是不合格。同班有一男生,用“定点大法”(就是把别人做好的图放在下面,用铅笔在上覆的白纸上定位,再把这些点连接起来)描出的图却每每获得老师好评。同班的男同学戏称:“真是天妒英才!”
阿清名如其人,瘦瘦高高,骨骼清奇。阿清是典型的工科女生,做什么事都很严谨。有一年系里办春节晚会,我们班出了一个节目,两个男生唱《同桌的你》,阿清和小禧口琴伴奏。于是每天晚上熄灯以后,在走廊里练习口琴成了她俩的必修课。几个星期后,当《同桌的你》的旋律已经于所有的人都烂熟于心之时,两个人颇能同步了,每个音符也都吹在点子上了,可是总让人觉得缺点儿什么——看来科学家的严谨并不一定能产生优美的艺术。

作者为后排右二
同学们来自五湖四海,所以每年春节从家乡回来都要带很多土特产。有时候是一些自制的点心,有的时候是一罐子咸菜。江南的学生常带自家灌制的香肠,北京的冬天天寒地冻,不需放冰箱,只要挂在阳台上,冻得铁棍一样。男生们每每下了晚自习,饥肠辘辘,便从阳台摘下一根香肠,就着冰碴儿和浮尘大嚼,不需任何佐料,是天然的美食。
印象最深的是山西的“石头饼”。据说是把发面揉好,擀成直径约一尺的大饼,贴在炉堂内滚烫的石头上烤熟的,因此饼上留有一个一个鹅卵石留下的凹痕。讲究一些的饼大概还有芝麻或者红糖夹心,有一种特殊的风味。饼很硬,需要掰着吃,是很好的零食。然而最使我不能忘怀的是小禧的奶奶自制的咸菜。不知道是什么菜,颜色黑黑的,浸在油里,吃起来很像橄榄菜。这种咸菜最宜就着炒米饭吃。食堂炒米饭中的菜极少,也没有油水,基本上是大白米饭加上一点鸡蛋末子和零星的胡萝卜、黄瓜丁,寡淡无味,没有咸菜断不能下咽,吃快了有被噎死的危险。自从喜欢上这种咸菜以后,我天天买炒米饭吃。白白的炒米饭上盖上一撮黑黑的咸菜,拌着吃,是人间至味。
校园歌手
清华的校园歌手是全国有名的。
我在UCLA读博士的时候,跟一个北大才子聊天,偶尔提到在清华的中文系读过。他马上问我认识不认识“阿飞姑娘”,仿佛你即使不知道清华有个中文系,也应该知道有个“阿飞”一样。
其实,阿飞不仅是我读环境系时的师姐,也是我在“编双”时的师姐,大我三届。我们住在同一栋楼里。我每晚睡觉前洗漱的时候,必要经过阴暗潮湿的走廊,然后经过她的宿舍。她一般是披散了长发,搬把椅子坐在宿舍门口,抱着一把吉它,用凄厉的高音唱着不知所云的歌。阿飞是个子不高,大眼睛的女孩儿。眼神时常显得迷离涣散,带着一点胆怯的纯净,仿佛在自己的世界里梦游。
当时免费听过阿飞姑娘多少歌,竟未觉得十分珍惜,后来阿飞都全国巡回开演唱会了。她的乐队有个响亮的名字,叫“幸福大街”,有着非常帅的吉他手。最激动人心的是,江湖谣传迷笛音乐节上,当阿飞姑娘走下舞台,崔健老师一个箭步冲上去握住她的手,万分感叹地说:“我老了,无所谓了,你们还年轻……”
崔健的确是老了。现在的“90后”、“00后”们知道崔健的人恐怕不多。
记得几年前去机场接老公,莫名其妙地看到一群中学小女生拿着摄像机、鲜花守候在机场出口,围得水泄不通。远远看着崔健走过来,才恍然大悟——想不到摇滚乐在年轻人中间也那么受欢迎!及至崔健走过,竟无人能识。随后走出两个不知名的韩国明星。一时间,人群如潮地涌了上去,簇拥着那一对俊男美女出了机场门。此刻再回过头去看崔健,他正跟一个朋友聊天,点了一根烟抽着,脸上难掩地流露出一丝落寞。
做摇滚乐的人大概都要面对这样的尴尬和窘困。他们写真诚的、触动人灵魂的音乐,却永远处于非主流的地位。不过“非主流”对摇滚音乐人来说也许是值得庆幸的——任何“主流”的东西最后都免不了流俗。不知阿飞现在是否还在坚持她的音乐梦想?
一直觉得阿飞的歌词写得比她的音乐好。印象最深的一首叫做《粮食》,有强烈的色彩和质朴的意象,带点儿海子诗的味道:
“你在黑黑黑黑的土地上,
种出金色金色的粮食,
你用金色金色的粮食,
换回苍白苍白的我。
我要坐在高高的粮食上,
想象我的红嫁衣,
我要守住金色的粮食,
守住一生的幸福。”
多年以后,一个人漂泊海外,再听到阿飞的音乐时,仿佛又看到那个小个子的大眼睛女孩儿,穿着长及脚踝的格子裙,大大的裙裾随着长发在风中飘扬。
拉拉杂杂地写了这么多。清华的岁月,隔了二十年的时光,从模糊的影像渐渐变得清晰。清华的开放和包容,使得她的学生能够以各样的方式绽放;清华人的严谨和坚韧,正像校训中所说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也成为我的人格中重要的一部分,使我在离开清华的日子能够砥砺前行。
作者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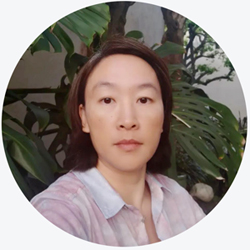
吴海平,1996年进入清华环境系,2000年从环境系毕业后转入清华中文系编辑双学位。从“编双”毕业后在清华中文系对外汉语中心(IUP)工作。之后在UC Santa Barbara 获语言学硕士,在UCLA获语言学博士。现任教于加州州立大学长滩分校(CSULB)亚洲和亚裔研究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