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他因对明代“一条鞭法”的研究享誉学界,被称为“明代赋役制度的世界权威”;
1958年,在中山大学“红专大辩论”运动中,他被树立为“只专不红”的典型;
1966年,因与吴晗关系密切等原因,他成为“文革”期间中大首批被猛贴大字报的学人。
他就是我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奠基人梁方仲。他一生致力于农业经济研究,发表了大量学术论著,为经济史学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他又是一位摆脱世俗功利、特立独行的学者,始终保持独立自由的精神,坚持以学术安身立命。
今年是梁方仲诞辰110周年。本期《南方》杂志将带你走进梁方仲跌宕起伏的一生,领略一代大师风范。

学贯中西,一代经纶独贯穿
1908年,梁方仲出生时,其父梁广照——清代广东十三行行商后代,事业颇顺,官运向好,于是为其子取名嘉官,号方仲,希冀其子日后加官晋爵,光宗耀祖。但梁方仲少年时代就显示出独立自由的性格,拒用此名,一直到病逝仅以方仲行世。
自幼受家学熏陶的梁方仲,国学根基深厚,一生喜爱诗词,经常背诵,不时作诗。11岁时,他就写下“壮志何时遂,昂头问太清”等诗句,被人笑称少年老成。
当时,西方的新思想、新文化已逐步传入中国,在年轻人心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梁方仲深受感染,逐渐意识到将来唯一出路在于自己,不能依赖上辈的余荫。于是,他坚决北上求学,以求新知。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反对帝国主义的浪潮汹涌澎湃。梁方仲就读的北京崇实中学的校长(美国人),因干涉学生反帝活动,动手打学生,引起学生愤怒。为示抗议,梁方仲与十多位同学愤而退学,转赴天津南开中学。一年后,他以高中一年级学历考入清华大学。
中学阶段,他受好友影响,很早便懂得“民以食为天”的道理和中国长久以来属农业大国的现实,深信中国农业问题的极端重要性,立志要为中国农业问题的解决出力,因此报读了清华大学农学系。不料,入读一年后,因学生不足,学校裁撤了农学系等四个系。后来,梁方仲转读经济系,因为他认为经济学和国计民生关系密切,农业经济问题当属该系教学和研究的重要范畴。
从经济系到经济研究所,梁方仲求学于清华大学的七年多,是他人生道路的重要部分,也是清华大学最好的历史时期之一。其间,梁方仲受到了严格的训练和磨炼,充分吸收了清华学术的精华,得到了清华学风的熏陶,也坚定了他终身奉献学术和教育事业的志向。在校园内严肃活泼的氛围里,梁方仲结识了数十位师友,在其离开学校后仍有往来、互助不断,其中就包括吴晗。
1933年冬,梁方仲进入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院研究所工作;1937年6月,东渡日本进行学术考察,因卢沟桥事变突发,毅然决定提前回国;1944年9月,应聘前往美国哈佛大学作为期两年的研究;1946年9月,转往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做研究……其间,梁方仲既承继了深厚的国学基础、文史功底,又受到了西方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的专业训练,可谓博古通今、学贯中西。
哈佛大学教授杨联陞在《赠方仲》一诗中,这样评价他:“北国学者莫之先,一代经纶独贯穿。”

1934年,梁方仲(左二)与谷霁光(左三)、罗尔纲(左四)、汤象龙(右一)、吴晗(右三)等在北京成立里史学研究会
“小题大做”,奠基中国社会经济史学
在学术界只要提及“一条鞭法”,就会自然地联想起梁方仲。
“一条鞭法”是明代嘉靖时期确立的赋税及徭役制度,由于制度推行从开始至结束,前后拖延时间很长,各地又采用了不同的变通形式、头绪纷繁,所以研究起来十分复杂。梁方仲运用大量的文献资料尤其是方志资料进行开创性尝试,抽象出规律性的内涵,才使得人们对明代“一条鞭法”有了比较完整的概念。
在长达四万余字的论文《一条鞭法》中,梁方仲以锐利的眼光考察了明代田赋制度的变革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指出“一条鞭法”是现代田赋制度的开始,打破了两三千年实物田赋制度,标志着中国货币经济的兴起,显示出16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
1936年,《一条鞭法》一经发表,马上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重视。次年,论文就被翻译成日文,在日本重要杂志持续刊载,译者称其为“明代土地租税制度研究少壮学者”。1956年,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将《一条鞭法》和《释一条鞭法》两文合并翻译为英文本出版。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费正清专门为英文本撰写前言,高度评价了这一著作的价值。
以“一条鞭法”为中心,梁方仲展开了对明代田赋制度的全面研究,他先后发表了《一条鞭法》《释一条鞭法》《明代一条鞭法年表》《明代一条鞭法的论战》等一系列论文。直到今天,这些文献仍然是学术界公认的该领域最高水平的研究,美国学者何炳棣教授称其为“明代赋役制度的世界权威”。
对明代粮长制度的研究,梁方仲也同样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明代粮长制》出版前,人们对粮长制不甚明了。正是梁方仲对粮长制度产生、演变和破坏过程严谨的论证,澄清了长期以来由于记载含混而在人们头脑中形成的诸多误区。该书近10万字,系梁方仲在世时正式出版的唯一一部专著,是他前后经过20多年的反复思索和研究的成果。但由于其学术取向与当时的中国史学的主流格格不入,因此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影响甚微。直至近年来,其价值才得到重新认识。
梁方仲最后一部巨著是脱稿于1962年的《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此书上起西汉,下迄清末,首尾两千余年。对历代户口、田地、田赋分门别类,综合编辑,制成统计表格235份,为研究王朝时期中国社会经济建立起一个可以通过数字去把握的基础。全书将近百万字,有着极高的学术价值。遗憾的是,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此书出版时已经是梁方仲去世10年后了。
回望梁方仲一生的治学生涯,不得不提“史学研究会”。1934年,梁方仲和志同道合的吴晗、汤象龙、罗尔纲、谷霁光、夏鼐、朱庆永、刘隽、罗玉东和孙毓棠等10人发起成立“史学研究会”。研究会明确宣示“我们认为帝王英雄的传记时代已过去了,理想中的新史乃是社会的,民众的”,并提出三大主张:一、研究整个民族主体的社会变迁史;二、先有专门的研究,然后才有产生完整历史的可能;三、注重史料搜集,没有大量的历史资料,是不可能写出好的历史的。
这些主张在当时是振聋发聩的声音,梁方仲对此终生服膺,孜孜以求。在总结梁方仲的治学方法时,他的学生曾经用“小题大做”来概括。所谓“小题”是指从个别研究着手。所谓“大做”:一是大量搜集资料,充分掌握全面的历史事实;二是把研究某一具体专题置于时代经济状况中作综合考察,以求得对整个社会经济特点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
虽然梁方仲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一条鞭法”研究,但他还有着更为宏大的计划——在田赋史专题文章的基础上,先完成《13-17世纪中国经济史》,继而撰写《中国田赋史》,再写《中国经济史讲义》,构建他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学术体系。梁方仲在学术上的根本关怀,是要去理解和解释传统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及演变逻辑。
醉心新知,不辞长作岭南人
1949年1月,梁方仲离开中央研究院,从南京回到广州侍亲。应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之邀,梁方仲任岭南大学经济商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创办岭南大学经济研究所。
在广州解放前夕,梁方仲还作出了一个关乎一生的重大决定。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代理部长叶公超曾专门到岭南大学动员他,并表示梁方仲熟悉的朋友已经或即将到台湾,如果他同意,就能立即安排交通和其他事宜,必要时将动用专机。同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来函邀请梁方仲去任教。对于这些“邀请”,梁方仲没有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便拒绝了,其中的重要考虑就是自己追求的学术研究在境外颇难开展,起码资料条件尚无法满足。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岭南大学被撤销,梁方仲转到中山大学历史系。当时的中大历史系,师资阵容强大,特别在中国古代史领域,有以陈寅恪领衔的“八大教授”之说,梁方仲就位列其中。
学经济出身的梁方仲,转入历史系后,深感当时形势下,需要更全面的知识,他经常求教校内外的方家、同事、朋友。他与陈寅恪的交往,充分反映出其认真谦和的作风和不断追求新知的精神。
1953年至1955年间,有“教授之教授”之称的陈寅恪,在中大开了《两晋南北朝史料》《元白诗笺证稿》两门课,每周两次,每次一节课。在陈寅恪的课堂上,梁方仲恐怕是最认真的一位。从他留下来的两本课堂笔记来看,陈寅恪当时开的两门课他都听了,除特殊原因缺了几节外,全部课时都到堂听讲。而且课堂笔记工整,极少涂改,课后还看参考书。两年下来,每门课分别记了两三万字的笔记。
值得一提的是,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开始,他在岭南大学和中山大学开设中国经济史课程,系统讲授从上古到明清时期的中国古代经济史,这门课是新中国大学历史系最早开始的中国经济通史课程。
1959年,新中国高校首次正式全面施行研究生培养制度。梁方仲是首批被指定为导师的人,他以极大的热忱与责任感投身到培养研究生的工作中。到20世纪60年代初期,他率先在全国综合性大学中同时培养四名(共五名)明清经济史专业的研究生,亦是中大历史系教师中带研究生最多的教师。
梁方仲从当时高等教育的实际情况出发,培养了一代在明清经济史研究领域有突出贡献、享有国际学术声誉的学者。
书生本色,“要当官就不要当我的学生”
1958年3月18日,中山大学全校师生在风雨操场举行了“双反、向又红又专大跃进”的誓师大会。
在此前的“整风”“反右”中,梁方仲除参加必须到会的政治学习外,仍遵其“读书、研究、授业、交友”一贯思路行事。没想到,在这次运动中自己一下子成了大字报、批判会的主要对象之一,并被作为“白专”典型来狠批,原来的正常工作秩序被打乱。
他的儿子梁承邺在回忆起这段历史时,认为其最重要的原因是父亲梁方仲有悖“又红又专”的言行流传颇多,影响“恶劣”。例如,梁方仲认为“搞好本职工作就是红,就是政治”“老老实实做研究就是唯物主义”,更在学术与政治关系上宣传他的一套想法——学术是有永久性的,而政治只能着重当前的问题。
当时的《中山大学周报》提到梁方仲有“三怕”“三重”的错误。“三怕”指怕开会、怕听报告、怕参加政治运动;“三重”指重学术过于政治,重业务修养过于政治品质,重个人交情过于政治立场。
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中,梁方仲依然不改书生本色。在积极授业悉心育人的同时,更是勤于著述,写出了大量论文。在“红专大辩论”时,梁方仲曾就自己“不突出政治”的问题做了表态,表示今后政治上应积极些。事实上,在随后多年里他那种以学术安身立命的观念始终坚定不移。
“红专大辩论”后,紧接着的是学术思想批判及推倒“旧”教材,由学生编写“新”教材。根据中大历史系教授蔡鸿生的描述,梁方仲对陈寅恪先生当年的处境深表同情,他曾在一次小型座谈会上,劝说过青年教师不要乱起哄,从此便有一句梁氏名言不胫而走,即“乱拳打不倒老师傅”。在他心目中,没有看或者看不懂“寅恪三稿”的人,是毫无资格七嘴八舌的。
在梁方仲与梁承邺父子间平常的交谈中,梁承邺知道父亲一向不热心政治活动,不想承担行政领导工作,鄙视希冀从政治地位提高、行政权力增大方面来促进个人业务发展以致获取个人名利之做法。他认为,参加政治党派会受组织纪律和有关政治要求的约束,特别是政治活动多了,教学科研本职工作的时间势必大受影响。
梁方仲不仅自己这样行事,还力劝朋友、学生搞学术不要三心二意,最好不当领导,更不要从政。1963年,他的学生叶显恩被推为中山大学研究生学生会主席。梁方仲知道后,唯恐学生对社会活动产生过多的兴趣而滋生官瘾,离开了学术道路,于是就找叶显恩作了一席语重心长的谈话,甚至说“要当官就不要当我的学生”。
叶显恩还谈到一件使他无法忘怀、终身受益的事。当“文革”轰轰烈烈开展时,梁方仲想尽办法将他的研究生毕业论文藏入不为人所注意的羽毛球盒内,才躲过“文革”被抄走的劫数而被保存下来,才使得他坚定地走向学术的道路。
除了热情奖掖研究生,梁方仲也热心负责地投身到各种授业育人活动中,积极参与青年教师和本科生的培养。
梁方仲不仅开创了中国社会经济史学,而且终生为这门学科的拓展完善作了无怨无悔的奉献。在数十年的上下求索中,清高之节,始终如一。可惜天妒英才,1970年5月18日,梁方仲被病魔夺去生命,于中山大学一地窖中溘然辞世。但他的研究,经历了半个世纪,至今仍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
————————————————————
梁方仲生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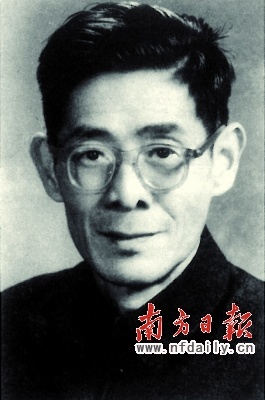
1908年7月19日 出生于北京
1911年底 随父亲回归故里广州
1922年 回到北京上小学、中学
1926年 考入清华大学农学系,次年转读西洋文学系,1928年再转读经济系
1930年 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
1933年 从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获法学硕士学位,任职于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
1934年 与著名历史学家吴晗等人成立“史学研究会”
1937年 赴日本考察
1943年 获哈佛燕京学社研究奖学金资助,次年赴美国从事研究
1946年 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从事研究工作,其间以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的身份,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一次大会
1947年 回国,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研究员,次年任代理所长
1949年 应岭南大学邀请,任岭南大学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
1952年 岭南大学撤销后,被聘为中山大学历史系二级教授,兼任中山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和广州市政协委员
1970年5月18日 逝世
————————————————————
延伸阅读:
梁方仲: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重要奠基者
——专访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历史系教授刘志伟
《南方》杂志全媒体记者丨刘龙飞
梁方仲先生是我国社会经济史学科的奠基者之一,他以其扎实的文史修养和良好的社会科学造诣,从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结构的大处着眼,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多个领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构筑起关于中国传统经济运行的解释框架,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范式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在梁方仲先生诞辰110周年之际,重温这位理论学人在学术研究上作出的开拓性贡献,能给我们带来哪些启示?《南方》杂志记者采访了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历史系教授刘志伟。
开拓探索中国社会经济史的新路径
《南方》杂志:为什么梁方仲先生会选择“一条鞭法”进行如此深入的研究?
刘志伟:我的业师汤明檖先生曾是梁方仲先生的助手,我第一次听汤明檖先生介绍梁方仲先生时,首先记住的就是“一条鞭法”这个名词。
1936年,梁方仲先生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发表《一条鞭法》一文,以后又陆续发表多篇相关论文,这些论著,几十年来被学界公认为“一条鞭法”研究最具权威性的经典之作。可以说“一条鞭法”研究,是梁方仲先生成就其学术功业的基石。
梁方仲先生走上史学研究道路,是出于对当时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的关切。他本来学的是经济学,1952年转到中山大学历史系以前,他也一直在经济学研究与教学的机构。但他选择了明代财政经济史作为研究园地,是由于他很早就认识到,要了解中国经济和社会,必从农业和农村经济入手,而田赋制度是中国农业和农村问题的一个关键,近代田赋制度是从明代“一条鞭法”开始的,所以他希望能从明代“一条鞭法”切入,形成对中国近代经济诸问题具有历史深度的认识。
“一条鞭法”的研究对社会经济史学界影响也很大,比如我研究“一条鞭法”后户籍制度的变化与广东地区乡村社会结构变化的关系时,就是从梁方仲先生那里得到的启发。可以说,梁方仲先生对“一条鞭法”的内容和实质的把握,包含了许多深刻的见解,被学界认为是“最为全面和深邃”的研究。
《南方》杂志:为什么说他是我国社会经济史学科的奠基人?
刘志伟:梁方仲先生是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科的重要奠基者。在20世纪以前,传统的中国历史研究,并没有中国社会经济史这样的研究领域,正是梁方仲先生等人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开创了这一学科,并且在这一领域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
他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从王朝国家的赋役征派入手,着力于户籍、地籍、田赋、差役、货币、漕运、仓储诸制度,探究王朝国家财政与乡村基层社会的运作机制,以及社会经济各个方面发展的性质。这样一种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路径,以王朝国家贡赋体制为重点,与中国古代正史中的“食货志”传统一脉相承,同时又嵌入现代经济学理论、概念和分析性研究的范式,开拓了立足中国历史经验探索社会经济史的一种路径。
对现代中国社会问题的关注是研究的出发点
《南方》杂志:如何理解他“小题大做”的治学风格?
刘志伟:梁方仲先生既是一位受过正规经济学训练的历史学家,又是一位具有深厚文史造诣,长期在史学园地耕耘的经济学家。他的研究,大多从明代赋役制度入手,不过,他在学术上的根本关怀,他所有研究的着眼处,是要去理解和解释传统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及演变逻辑,对现代中国社会问题的关注是他研究历史问题的根本出发点。
“小题大做”是梁方仲先生所推崇并一生实践的研究风格。所谓“小题”,是指从个别研究着手。所谓“大做”,有两个意思:一是大量搜集资料,充分掌握全面的历史事实,务求本末俱备,源流兼探;二是把研究某一具体专题置于时代经济状况中去作综合考察,以求得对整个社会经济特点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这在梁方仲先生以“一条鞭法”为中心的研究中,已经得到充分体现。梁方仲先生的遗稿中,包括一批读书札记和讲义的草稿,让我们对梁方仲先生在研究中如何“大做”有了更丰富的了解。
对于治史之人来说,读书广博,惟求其“通”。而这个“通”,正是达到第二个意思的“大做”所必须具有的素质。梁方仲先生的社会经济史研究,之所以能够“小题大做”,同他长期在读史求通方面所作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南方》杂志:梁方仲先生主张多从地方志、笔记及民间文学如小说平话之类中去发掘材料,这对他的研究有何影响?
刘志伟: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还处在拓荒阶段,很多青年学者提出要重视地方志资料的利用。梁方仲先生可以说是利用地方志资料来研究王朝制度与地方社会最为成功的学者之一。为了弄清楚“一条鞭法”在地域上的发展以及各地施行的实况,他利用了从中国各地和日本、美国等国家收藏的地方志超过1000种。正是因为大量利用地方志资料,使他得以掌握“一条鞭法”在地方上推行的过程、内容的精粗差别以及不同地区的社会实况。在当时中国历史学研究者中间,很少有像他这样大量利用地方志资料的。除了地方志资料以外,梁方仲先生还特别重视各种公私档案、民间文献和实物证据的搜集、研究与利用。
沿着他开拓的学术道路不断努力前进
《南方》杂志:在梁方仲先生诞辰110周年之际,重温这位理论学人在学术研究上作出的开拓性贡献,能给我们带来哪些启示?
刘志伟:梁方仲先生的研究,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历久常新,几十年来一直保持其生命力。他提出并努力探讨的许多问题,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最新发展中,正在成为许多最前沿研究的出发点。
2016年11月,为纪念梁方仲先生的经典著作《一条鞭法》中文版发表80周年,以及作为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丛刊第一种的英文版出版60周年,我们与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合作,在上海的哈佛中心举办了一次小型研讨会。这个会议没有采用惯常的各人报告论文并评议的方式,十多位对中国古代贡赋经济有专门研究的青年学者聚在一起,就如何继承梁方仲先生开拓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传统,从财政问题入手推进贡赋经济体制研究的深化,展开了充分讨论。讨论涉及多方面问题,提出许多新颖的思考和认识,让我看到新一代学者的努力,已经在这个方向上取得了许多新的进展,令人振奋。
历史学的很多研究都需要几代人的不断努力。当中国历史学反省过去几十年走过的道路,重新寻找新方向的时候,我们重读梁方仲先生的遗作,重新思考梁方仲先生在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所提出的问题和在研究方法上的探索,对于重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体系、新范式,一定可以得到许多启示。我认为对梁方仲先生最好的纪念,就是沿着他开拓的学术道路不断努力前进。
————————————————————
梁方仲的朋友们
文丨梁承邺(梁方仲之子)
诚如著名历史学家朱杰勤所云,父亲“以读书、交友、著述、讲学为乐事”。父亲的确乐于交友,极重友谊。我记忆中,尤其在其案历所记文字以及其他文字材料反映出来的情况,在中大他较有交往的朋友数十人,包括不同年纪、不同处境、不同特点的人。
岑仲勉是中大历史系的老教授,比父亲年长十多岁,与我祖父祖母原来就有来往,父亲称岑氏为世丈。岑氏虽然“半路出家”,开始专门从事史学学术研究的时候已近其人生之中年,然勤奋异常,著述宏富,是闻名遐迩的隋唐史专家。一直以来父亲与岑氏关系较好。早在抗战时期,由于社会科学所与史语所都搬迁至同一城市相近处,父亲与岑氏的直接交往便开始。20世纪30年代末,父亲就曾抄录其诗作呈送岑氏。新中国成立后,两人皆任教于中山大学历史系,又同属中国古代史教研组,因此,在生活与业务上,彼此交往切磋较频繁。20世纪五六十年代,父亲所写的论著、讲义,就曾认真参阅过岑氏的著作。1961年岑氏辞世时,父亲写了挽诗痛悼。
父亲与著名历史学家陈序经,严格来说,在1949年前彼此仅认识而已。1949年后于岭大、中大时期,他们相互了解逐渐加深,情谊不断增长,最后成为无话不谈、倾力相助的莫逆之交。岭大时期,父亲对陈氏的知人善任、从善如流、深入实际的工作作风,全心全意办教育、努力创建一流大学的宏愿与贡献深为佩服。1952年院系调整后,陈氏从原来一校之长的位置下到历史系当一名普通教授,使很多人吃惊的是,他坦然面对,专心致志,全身心投入东南亚古史等的研究与著述中,短短几年中有关著作陆续脱稿。看到在逆境中一个真正学人本色的闪烁,先父不能不为陈氏的人生态度和深厚的学养所折服,从而主动与之亲近。
自院系调整后,父亲与陈序经同在一系,彼此间由相识到相知,情谊油然变笃。这种友谊诚如欧阳修所说的“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后来许多资料都表明他们在工作上、思想上、生活上乃至经济上皆有“同道”互助的表现。父亲由于长期勤于工作又不善调理身体,不时患病,多次入住中大护养院(卫生院)或赴市内医院就诊,陈氏见此,便引荐一些很有经验的医生为父亲治病。因而父亲结识了中山医学院许多著名医生、教授。我祖母患病时也曾得到陈夫人介绍一金姓中医师。为了使父亲能劳逸结合,摆脱终日疲劳、身心不堪重负的状态,陈氏多次邀父亲乃至我们家人参加由其领队或组织的休养团或参观团。
当然,他两人之间频繁的交往最根本的基础在于思想与工作的交流互动。陈氏20世纪50年代着力撰写《东南亚古代史丛书》,据父亲说,陈氏曾将该丛书的部分手稿,先请他阅过并提些参考意见。
梁宗岱时任中大外语系法文教授,他留学法国多年,法文(语言文学)水平很高,且新诗造诣殊深,为著名的新月派诗人之一。
1961年我由武汉大学放暑假回到广州,8月间参加了一次中大教工及家属赴湛江的休养团。往湛江船上,我有意向梁氏问东问西,当我说到印象中复旦大学在1952年院系调整前的声望远不如今天那么响亮,他马上说,此言不差,不过自他在抗战时去复旦后,该校情况顿时改变不少,因为校长魄力与眼光不够,后来,校长接纳了他不少建议,特别是广揽出色教授(如他这般的人),情况当然就不一样了。父亲在旁听此,故意笑梁氏在“吹牛”。梁氏一听,顿时脸色骤变,愤愤不平对父亲还击:“亏你讲得出口,我30年代初就在北大当了教授,可惜你当时在清华,若在北大的话,你可能还是我的学生呢!”言下之意,要父亲马上闭口。
游览湛江名胜湖光岩登山时,梁氏一马当先,快步先上了山顶,我与父亲漫步随后才到。我敬佩地说:“梁伯伯,你身体真行。”对方马上答曰:“当然啰!这里没有人,包括你们年轻人也无法跟我比,不信,我们来比赛一下?”随之摆出一副要来个真正比赛的架势。大概平时太熟,随便惯了,父亲又忍不住脱口一句:“你又在吹牛!”这一下子,可惹怒了梁氏,他马上斥责,并摆出举拳头状:“你尽在挑刺,跟我作对,真想揍你一顿!”当然这是朋友间的耍闹而已,回想此一幕,反而为他们尽显孩子般的童真表现而高兴,不时回味之。事实上,斗嘴后芥蒂很快就烟消云散,友谊照旧。
(本文摘自梁承邺先生著作《无悔是书生——父亲梁方仲实录》)